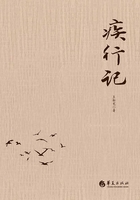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政工组的“累活”
“文革”期间,原有的党委、政府机构被“砸烂”了,全省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省革委会,下设了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和外事组等办事机构,企业也上行下效,无论工厂架子大小也都叫“组”,厂部一般设政工组、生产组、技术组、供销组和财务组等。说到我们厂,是政工组与厂领导同处一室,背景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特殊性”和“可靠性”,把政工组排了在前面,让我们享有与书记、厂长一起办公的“待遇”。
当年,厂部办事机构人事安排是:政工组组长黄君美,生产组组长谭显南,技术组组长张善林、副组长黄飞,供销组组长吴仕週、副组长钟卓君,财务组组长欧丽生、副组长袁连发等。这几个办事组都挤在同一层楼办公,说话声音大一点谁都听得到,管理部门之间也常有扯皮摩擦,但氛围还是挺和谐的。当过空军教官的黄飞口才很好,经常在出差回来后宣讲路上的趣闻,比如关于建三峡水库的传闻,说一旦溃坝武汉等长江沿岸大城市将会毁灭,等等,大家听后既兴奋又紧张。
1976年7月,我脱产担任了厂专职宣传干事。政工组的主要工作有:党务、劳动工资、人事档案、奖励惩处、宣传教育、计划生育、工青妇、工会等。两年后的1978年11月,我担任厂政工组副组长。
黄君美同志是政工干部的模范,她做事一板一眼,党性观念很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天都早来晚走,是那一代人任劳任怨的缩影。工会干事苏章玲,原来在东莞的国企工作,是一个勤勉、正直的干部。保卫干部聂忠健与妻子伍丽妍一起,从部队的文化单位转业,夫妻俩继承了部队的好作风,工作认真负责。宣传干事李小眉,性格温和,写得一手漂亮的字,父亲是华南师范大学的老教授。
每逢厂里开大会都由政工组来组织。那时候条件很简陋,没有固定统一的座椅,有些人自备了木轱辘、小凳子,使劲往会场四周、门口靠,每次开会都得费一番唇舌整顿场面。后来我想了个法子,向老木工梁师傅建议,从机器包装箱拆下来的垫木条,别拿来当柴火了,利用它们做成长条靠背椅子,每张能坐4~5人,有几十张这样的椅子就足够了。三四百人能够整整齐齐地坐着,开会的散乱现象有了明显的改观。
设立厂图书室。我们与邻居庙前西街新华书店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当他们要到外面搞书市活动,我们就帮忙搭铁架棚子,凡是有新书到了,店里都留一些,让我们从中挑选一部分,因此当时新出版的通俗文化类书籍,厂职工都能借阅到。
播音室设在综合楼二层,除每天定时转播省、市广播电台节目外,还及时广播厂里的好人好事,稿子由各车间通讯员提供。上面的两件工作我还在车间时就兼上了,这也耗去自己不少时间和精力。
有一次,我从播音室回到车间,职工问我,你听到了吗?电台今天表扬我们了,讲的时间还挺长。我忍不住笑了:“是我讲的,听不出来吗?”“是吗?真像电台播的!”可见,每次都得认真啊,还真有职工在听呢。后来,我也实在顾不过来了,就把这两项工作交给了其他青年团员,她们学习了图书馆的管理办法,为职工服务得挺周到细心。
要说最费劲的事,要数遇到休息日集中收听“最新指示”或“两报一刊”社论。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只有少数职工家附近有公共电话,如果有事多数靠直接到家里通知本人,如果碰上家人都不在,还要多说些好话请邻居帮忙转告。
广州城区,是随着古珠江水道、网河演变发育而成的,因而大街小巷的走形,也纵横交错七扭八拐的。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到职工家里通知事情,在海珠区找龙导尾巷,结果被路人指到了龙套尾巷。嗨!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住巷前头的住户,有的还不知道巷尾的街道叫啥名,还有其他职工等着通知呢,真让我急得不行。
就这样,十几人分头累死累活跑大半天,把全厂的人都通知齐了,等到晚上八九点,高音喇叭响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就几句话工夫,“收听广播完了,散会!”这时候职工犯愁了,这么晚了哪有回家的公交车啊,有的人只好在车间熬上一晚上,第二天还得照常干活。就这么折腾,当时也没人敢说什么。
1978年后,开始落实各项政策,以消除“文革”极“左”带来的“遗患”,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全面清理职工档案,这关系到每个职工特别是老职工和他们家属的政治生命。
一直以来,干部职工入团、入党,都要经过严格的外调和政审。按规定,单位人事档案都不外借,只能在管理部门内调阅。如何筛选、摘录档案里的内容,这很体现外调人员的政策水平和文字能力,且这些资料提取后一旦归档,就成了个人历史新的证明材料。我在清理档案时,如同在看人间一幕幕命运沉浮、荣辱交替的悲喜剧。
我们厂从1958年成立起至1966年初,上级管理部门是民政局生产教养科,直到民政工业公司成立后的1966年1月,才结束被“生产教养”的历史。单位不大,但由于历史原因,职工身份构成颇具复杂性、特殊性和多面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发生的巨变,对芸芸众生的影响让人感慨不已。这里有被称为“三代贫农四代乞丐”的城市贫民;有改造从良获得新生的女工;有上级部门派出的管理干部;有因伤病退伍的军人;有经甄别“不宜留用”的公安干警;有反右运动中因“说错话、站错队”被迫转业的军官;有爱说“牢骚怪话”从大厂清理出来的高级技工;有无依无靠的收容对象、劳改释放人员;有受当地迫害回国的海外归侨;有举目无亲的孤儿院学员;有为了找“饭碗”的应届毕业中学生……看过这些档案后才知道,有些人“身怀绝技”却深藏不露,有些人一表人才内里却“劣迹斑斑”,展现在我面前如同斑斓十色的“小社会”。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事外,职工也有犯难的小事直接找来的,我从不往外推,记得就有两次取巧“破案”的事,还挺有戏剧性的。
一天中午,拄着单拐的生产组组长老谭来找我,说他在厂里丢了块手表。我一听,这可麻烦了,当时手表属贵重东西,国产手表也相当于学徒工三四个月的工资呢,能找回来吗?我安慰他不要抱太大希望了。
那天也巧,快过午休时间了,我想起曾见老谭在喷漆车间门口洗手,莫非他把手表取下来搁在什么地方给忘了?我下意识径直走到那地方,眼睛环顾四周仔细寻找,没有。我正准备离开,眼光落在洗手处水龙头下的地面上,职工洗手后留下了一堆碱沙,皂泥浆里似乎有点发亮。我心头一紧,预感到是有什么东西,赶紧过去蹲下用手一扒,果然是个手表!失而复得让老谭喜出望外,他笑着说:“哦,我想起来了,在饭前洗手的时候没站稳滑倒了,是别人扶我起来的,估计就是那会儿把表给甩掉的。”
第二次“查出”的涉案人是“马仔”,这事我在“外篇”回忆文章里有详细记载,这里不赘述了。两次取巧“破案”,凭的是我对职工的了解,我对大部分职工的性格品行、能力特长和家庭情况都知个大概,这就是能够“临门一脚”的本钱。
1981年11月,在广州市委党校第一期理论班毕业后,公司党委任命我为东升电器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从1981年12月至1984年4月,我依旧与政工组的同志在一起工作。
兼任工会主席,多是围绕着职工的生老病死来忙活。诀窍是:脑子清、耳朵灵、跑得勤、端得平。计划经济的年代,没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土壤,职工的“获得感”大体是差不多的,这是那时候群众工作好干的主要因素。
我感到遗憾的是,多次去做“两口子”的思想工作,劝厂里闹矛盾的夫妻不要离婚,都无功而返。又几次受职工之托,为厂里的大龄青年牵线,也没有“终成善果”。怎么说呢,“婚姻”这本书,我可能一辈子都读不懂,何况那时自己还不是“过来人”呢,更不明白那些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家事,败下阵来就是难免的了。这我认了,需要体验的东西靠硬生生地想象是得不出来的。
那个年代的特点,偏重强调集体行动、集体作用和集体荣誉,每个人的个性、情感和偏好被厚实的工装严严地裹着。1980年前后,随着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萌动,政治、经济环境越来越宽松,社会活力逐步显现,工会也尝试着组织大家“外出活动”,这又成了挺稀罕的“职工福利”。
先是组织职工到珠海横琴岛“旅游”。在改革开放初期,那里还是一个荒海岛,杂草丛生、渺无人烟,却成了“走私”的理想集散地。这么说来,还有点神秘感,那里到底走私什么东西呢?其实也就两样:香皂、饼干。计划经济的代名词就是“短缺经济”啊,人民币10元一桶的嘉顿罐装饼干,2元一块的力士牌香皂都是紧俏货。旅游一趟,每人扛着几箱饼干、几十块香皂归来,兴高采烈得像过节一样,连带“干群关系”也改善不少,职工由衷地说我们给大家办了好事。
没多久,人们的兴趣转到了深圳特区,职工又涌向了沙头角的中英街。公司保卫科成了热门地儿,因为它有权确定各厂每天办理特区“通行证”的限额,职工如果能把外地的客人捎带上,更是显得有面子的事。在特区的人潮里,从一般生活用品如酱油、奶粉等,到牛仔裤、黄金戒指、项链和手镯,只要比内地市场便宜的都是抢购的对象。
不光毗邻港澳的广东,我的北方老家山西,改革的春风也吹活了人们心底的念想。地市的邮政局过去是计划经济里的传统老大,也感受到了潜在的危机,有了迈出步子改革搞活的冲动。其中凸显行业优势的,就是要让邮政储蓄“活”起来,对储户必须比传统银行更有吸引力。一些有进取精神的干部职工建议,到深圳沙头角买进一批黄金首饰,作为物美价廉的储蓄奖品,以增强对储户的吸引力。
山西的同志朴实厚道,一路南下省吃俭用,我热情接待并安排了住宿,翌日送他们上了往深圳的列车。虽然只是帮了家乡一个小小的忙,我心里也挺高兴的,要不怎么说故乡水家乡情呢。邮局的同志都觉得为公家办了件好事而高兴。谁料到,返回当地后,竟然被人告到了外汇管理部门,说这是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条例,带队到深圳的领导被迫停职检查了3个月。但上级很快发现了问题,还了蒙冤的同志一个公道。
这不禁让那些敢于“吃螃蟹”的人叹息,他们的结局往往成了事实上“改革有罪、开放无理”的注脚。我联想到1978年冬,安徽小岗村带头联产承包的18位老乡摁手印的事,当年改革开放可不是顺理成章的事,风险真的很大啊!
不是一直有人把非技术专业的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称为“万金油”干部吗?我倒认为叫“万能胶”干部更贴切些。因为,大到国家社会、小到社区乡村,组织上都离不开具有“黏合力”的干部,他们无论放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都善于找出各种问题的相互关系,把它们“黏”在一起形成合力。如果没他们,队伍就可能是一盘散沙,成不了大事。至于最终是否“黏”得牢固,那要看干部当下的政治品质、思想水平及工作能力等,当然还有起重要作用的外在因素。
思之得
有人说,大凡当过士兵的将军,都会爱护士兵。我的干部生涯,是从“副股级”开始的,我能感受“布衣”的喜怒哀乐,有种天然的归属感。“原生态”的实践,帮助我配对了排忧解难的“钥匙”。要说几十年工作中“真招、实招”,究其渊源或许就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