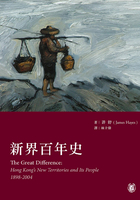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導論
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1)是香港殖民地政府高級官員,在1898年8月他花了十二天調查將劃歸香港的新租借地,歸來後,他用「巨大差異」這個說法來強調「香港與新界華人居民」之間的分別。但是,如我在本書第二章指出,這句話同樣適合用來形容這個面積現已擴大的英國直轄殖民地的兩個地區,即舊有和新增部分。我寫此書的目的,正是要探究這九十九年租期中的「巨大差異」。(2)
駱克在1879年獲任命為官學生,成為香港公務員,仕途扶搖直上,歷任要職,包括管理香港華人事務的華民政務司(1887)和輔助香港總督施政的輔政司(1895)。駱克身為華民政務司,與華人精英建立了更緊密和正式的聯繫,是熟悉華人事務的官員,能力和聲譽人所共知,因此,外交部委派他調查新納入香港疆域的租借地,向該部和港督提交報告。(3)
後來稱為新界(英文名稱為New Territories,但最初是用單數的New Territory(4))的地區,迥異於駱克時代的香港。當時這個殖民地的早期轄地只有香港島和九龍,是因為鴉片戰爭(1840-1842年)開始的連串衝突而割讓給英國。此時香港島受英國統治已差不多六十年,九龍則近四十年。每經過一天,它們離開傳統中國的內涵和心態就更遠,而新近納入香港領土的地區,就代表着這種傳統中國的內涵和心態。新界也遠比香港舊有的轄地為大,面積相當於後者的十二倍。此外,住在新界的八萬多名鄉民,很早以前就世居此地;相較之下,1898年時在英屬香港生活、工作或途經此地的二十五萬華人,是以男性為主,而且絕大部分漂泊不定。
英國租借新界的時期,絕非太平無事,英屬香港一直受國際和境內事件所影響。內部方面,這個在1898年後面積大增的殖民地,社會內存在兩個迥然相異的部分,有各自的變化發展,彼此創造出一種令人着迷、猶如陰陽的相互影響,(5)令香港歷史更引人入勝。這種相互影響在整個九十九年的租借期歷歷可見,但到了戰後初期尤其活躍,因為那時候新界成為了香港的土地供應來源,是香港進一步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及至英治時期最後十年,這種相互影響由於一些頗為不同的原因,又再度熾烈起來,當時原居民與更為人多勢眾的香港其餘居民發生嫌隙。導致這些齟齬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紀初為原居民而制定的法律和管理安排,另外還因為兩批居民有迥然不同的歷史和心態。
由於這個題目十分複雜,我認為先在導論簡介本書的題目和主旨,對讀者會有所幫助;另外還會提及一些我在預備寫此書時想到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也臚列在索引之中。
第一章討論1898年時的新界及其社會,涵蓋當地持續和長期的拓殖定居、多采多姿的歷史、緊密的社會組織,以及主要屬於自給型的經濟。第二章將這塊新租之地與它即將加入的殖民地相比較,藉此探討上述的「巨大差異」。另外會談及英國接管時發生的武裝反抗;還會提到新九龍,那是指位於九龍山脈下一帶的新租借地,此地區會被當成市區來管理。第三章討論1900-1905年的土地丈量和業權審定,這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按照中國風俗習慣,維持原來的土地擁有權,從而保留1898年前實行的制度的基本元素。(6)但首先會廢除某些「牴觸英國施政原則」的特點,(7)尤其是關於中國土地稅的組織和稅負歸宿問題,以及由中間人代收稅款的做法。
第四章論述港府在倫敦督導下制定管治新界的新制度,還有1941年日本佔領香港前發生的事件。之後第五章專門處理的題目,是1941-1945年的戰爭與日佔時期(由於各種原因,這段時期是新界和整個香港歷史的分水嶺)。日佔時期是慘痛艱苦的時期,但對後來的政治發展卻有重大影響,例如村代表選舉和鄉事委員會制度(在1948年開始),以及一些原居民社群及其領袖耐人尋味地捲入1967年跟中共有關的騷動。
第六章論述戰後頭幾十年間新界的狀況,在那個時代,農村的生活和經濟面臨徹底和根本的改變。由1950年代末起不足二十年內,稻米種植銳減(原因不只是香港轉向工業生產,並開始大規模發展),新界農村典型的自給型經濟從此結束,這種情況大有助於推動發展與現代化,新界山區也大多變成管理完善的郊野公園,為香港日益膨脹的都市人口提供休閒去處。另一個不同但對於促進發展同樣關鍵的因素,是上文提到的鄉村代表制度化,加上鄉議局在1959年重組,成為法定諮詢機構,從此官民可以就發展事宜彼此協商,互相保持靈活性和妥協,避免可能爆發的衝突。(8)同時,如第七章所述,為了向城市人口供應食水,1920年代開始了連串水務計劃,因此須搬遷一些鄉村,而在1945年後,因有四個大型水塘要興建,搬村工作的步伐就更加快了。這些農村居民被迫離鄉別井,去到完全改變的環境,這些情況對他們的影響,此書只能稍述一二,應當有人另作全面討論。
「新市鎮」是今天新界的重要特徵,第八章論述為規劃興建新市鎮及相關基礎建設(如公路、跨境連接道路,還有地下鐵路支線)的收地和搬村工作。此章也會談及補償政策的演變,這些政策如何影響鄉村地主,鄉村地主又怎樣看它們。在這個大舉搬遷鄉村的時期,鄉村領袖的務實態度,是令計劃目標得以實現的關鍵,搬遷鄉村是根據既定但有彈性的政策,不過總是靠協商來達成。挺過了這個變化過程的原居民,為來到他們的家園定居的龐大城市人口賦予認同感,並肩負領導之責。如上文所指出,餘下的新九龍村民得到的待遇十分不同,此章結尾部分會述及他們那段較為乖蹇的歷史。
第九章論述處於鼎盛時期的鄉村社會,以及鄉事領袖如何藉着新的地區諮詢委員會(9),帶頭建立與政府對話的理想新方式,並推動文娛體育項目,以滿足「新市鎮」地區的需要。鄉村團體也繼續舉行傳統節慶活動,從而在他們龐大的人口中,維持中國民俗文化的精神。這些功績是「巨大差異」的另一體現;因為英屬香港在涵蓋面、歷史深度和熱情方面,沒有什麼事物能與原居民社會充滿活力的文化傳統相比擬。(10)同時,在尚未發展的鄉村地區,香港的急速工業化和現代化,正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產生影響,雖然悄無聲息,但卻沛然莫之能禦,第十章會一一探討。
第十一章集中討論一個很不同的層面,即在1967年暴動期間,原居民群體內令人矚目的轟動事件,當時不少新界領袖及其追隨者堅決對抗港府,而他們採取這種立場並非北京授意。這種情況背後的原因,是中英兩國歷史遺留下來的潛藏怨恨,還有更為近期的影響,即1941-1945年日佔時期的事件。1967年的事件是一個謎團,應當予以更全面的探討,它們再次提醒人們「巨大差異」仍然存在。另外,在1982-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歸還中國管治,以及在1980年代末為日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草擬《基本法》期間,新界領袖為了維持原居民所積累的既得利益,大力展開游說活動,同樣令人感到「巨大差異」的存在。
在英治時代最後幾十年,香港新舊兩批人口趨於融合,但又矛盾地出現新的分歧,這些會在第十二章探討。那時候,原居民的外表和生活方式幾乎與其他人無異,但他們對於各種公共事務的反應,卻令他們與一般大眾「扞格不入」。他們罔顧環境和公眾福祉,令人側目並招致譴責;在社會辯論鄉村婦女的土地繼承權問題時,他們的行為,令人看得大搖其頭。對於原居民特權的不滿(這些特權常被濫用),以及鄉議局為維持這些特權而發起態度強硬的反政府運動,都令公眾愈來愈與這些老居民有明顯距離。第十二章涵蓋這些題目,以及其他仍在發展變化的問題,(11)這些問題一直延續到1997年以後,該章「後記」部分還會談到一些相關議題。

圖一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黏附地圖(HMSO publication: Treaty Series No. 16, 1898)

圖二 從香港島遠眺九龍、九龍山脈和大帽山(新界最高峰)(photograph by Hedda Morrison, copyrigh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圖三 位於青山附近的圍村泥圍,約攝於1930年(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四 1899年繪製的租借地分區地圖,First Year p. iii曾提到此圖(註冊總署田土註冊處提供,1963年)

圖五 新界一處山谷的冬景,約攝於1958年(香港政府提供)

圖六 城門大圍村,是在1928-1931年城門水務計劃被搬遷的村落中最大的一條(前荃灣理民府提供)

圖七 英方勘界代表駱克(正中)與中方勘界代表王存善(駱克左側)和其他中英官員,攝於1899年3月開會期間(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圖八 位於沙埔村的義塚,該義塚紀念的是1899年4月在反抗英國接管新界戰事中的陣亡者(蕭國健博士攝)

圖九 1899年8月2日港督卜力爵士到訪大埔(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圖十 港督卜力爵士到訪大埔時村民呈獻的頌匾(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他到訪屏山時,似乎也獲贈另一匾額:First Year p. xvi

圖十一 卜力爵士與駱克(兩人皆在正中)與屏山鄉紳父老會面(香港歷史檔案館提供)

圖十二 峰巒起伏。從這張照片可見,城門水塘的興建地點原本是群山環繞的農谷(photograph by Hedda Morrison, copyrigh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圖十三 1905年繪製的荃灣區測量圖局部,取自丈量約份第451約的集體官契(前荃灣理民府提供)

圖十四 助理田土官金文泰簽發的執照,證明某人擁有荃灣一幅土地業權,執照上有一些後來買賣土地時劃掉的資料(前荃灣理民府提供)。金文泰曾寫道:「我算過,我在不足一年內簽名簽了五十萬次,如有方法能減輕這件沉悶的苦差,那真是值得欣喜之事。」(C.C. to Hon C.S., 21.2.06)見本書第三章註70。

圖十五 1900-1904年間丈量土地和劃界時,大嶼山石壁鄉一幅土地業主所獲的「紙仔」(石壁鄉池長發先生生前提供的原件副本)

圖十六 南約理民府官史高斐(Walter Schofield)巡視大澳,約攝於1922年(史高斐生前提供)

圖十七 已歸化英國的英籍子民(1909):河上鄉的侯澤南(上水太平紳士廖正亮提供)

圖十八 婦女的艱苦命運:從醉酒灣岸邊運送材料到葵涌上方新構築的防禦工事,約攝於1939年(高添強提供)

圖十九 婦女的艱苦命運:每天往來於泥路上的客家婦女(photograph by Hedda Morrison, copyright: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圖二十 上水附近的地方公共工程,攝於1956年。大埔理民府官黎敦義與新界民政署長彭德(坐者)偕同妻子參加儀式,為毀於暴雨的陂堤重建落成揭幕(香港歷史博物館提供)
(1) 譯註:他原本所用的漢名是駱檄或駱任廷。
(2) 見Shiona Airlie, p. 103,以及本書第六章的註36。為期九十九年的租約始於1898年6月9日中英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終於1997年7月1日香港全境交回中國管治。關於《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文及地圖,見No. 25 in Hertzlet's China Treaties, Vol. I, pp. 120-122。這次擴大香港領土,表面上是為了軍事防務,自1884年起,香港軍事司令部的歷任將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英國強迫中國租借這片領土的直接原因,卻是當時的外交和政治形勢使然。見Andrew Roberts's Salisbury, Victorian Titan, pp. 687-689。英國根據1898年10月20日發出的樞密院令,把管轄權擴大至新界,而1899年12月27日頒佈的另一道樞密院令,則把九龍城也納入其管轄。
(3) 駱克在1902年獲委任為威海衛行政長官,威海衛是位於華北山東省的另一個租借地。他一直留在威海衛,直至1921年離任退休,他為此感到十分懊惱。駱克在1908年獲冊封爵士。他精通中文,愛好蒐集中國藝術品和古錢幣,撰寫學術著作,並且擅長行政。他三本最為人熟知的著作是《成語考》(A 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1893年出版,1903年出修訂版),三卷本的《遠東貨幣》(The Currency of the Farther East,1895-98),以及另一本關於他所收藏中國銅錢的圖錄(1915)。他的文件和藏品現在都藏於愛丁堡。見史奧娜·艾爾利(Shiona Airlie)所寫的駱克傳記(Airlie, 1989)。
(4) 柯美(G. N. Orme)在1912年寫道:「所謂的New Territories,更通行的稱呼是the New Territory,或簡單地稱為the Territory。」見Orme, para. 1。
(5) 關於「陰陽」簡單明暸的介紹,參見Lai, Rofe and Mao, pp. 191-192。
(6) 這次土地丈量和地籍整理,應當有人去全面研究,這不但由於它們是重大事件,還因為已發表的報告和論文(有時候很令人混淆和互相矛盾)對於某些問題不一定能提供答案,而在我撰寫本章時,這些問題一直令我困擾。有些學者認為,新界田土法庭的裁決,以及此後有關業權登記的殖民地措施,改變了地方上的習慣法,陳奕麟尤其持這種看法(Allen Chun, 2000)。這些問題會在第三章第82-84頁探討。
(7) 這句話出自金文泰之口,為一位早期的英籍理民府官在其《關於新界的報告(1899-1912)》中引用。見Orme, para. 21。
(8) 隨後的對話往往是吵吵鬧鬧,言詞莽撞誇大,但這是顯著的中國特色,大陸政府也是如此,例如在1990年代它不欲見到香港急於推行政制改革,與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齟齬時就是這樣。在地方事務上應用這種語言,則通常大大障蔽了務實態度和理智識見。
(9) 它們是在1977年於新界設立,五年後擴大到香港和九龍市區,改稱區議會,2000年其英文名稱改為District Council。
(10) 關於傳統農村文化的描述和闡釋,見Hayes 2001.1。
(11) 尤其是關於鄉村管理和鄉村選舉的問題,法庭裁定外來村民在這些事務上應有參與權,因此政府後來實行了多項改革。見本書第330-3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