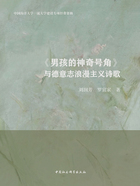
一 文本概述
华夏民歌见诸文字的可上溯到《诗经》。这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名为《诗》,因为汉代立于学官,成为五经之一,才被称为《诗经》,收入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作品共305篇,根据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从内容看,“风”是出自十三个不同地区的土风歌谣,共160篇。“雅”是朝廷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共105篇。“颂”则是宗庙乐歌,共40篇。《诗经》的作者大部分已经湮灭无考,所知应为两类人,“一是地位不同的文人,一是成分复杂包括奴隶、士兵、平民的民间歌手”。而“属于民间的诗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1] 接续 《诗经》的是“乐府”。“乐府”本是汉代主管音乐的官署,所出的诗歌以及后世的仿作就被称为“乐府诗”,也简称为“乐府”,其中有民歌也有文人作品。北宋的郭茂倩编了一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谣谚,共5000多首。根据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12大类。大部分是有主名的诗人所作的“拟乐府”,而属于两汉民歌的“古辞”夹在其中,共139首(其中相和歌33首,舞曲歌3首,散曲1首,杂曲歌58首,琴曲歌44首)以及“汉铙歌十八曲”中的若干。南朝乐府民歌是东晋至陈末的乐曲歌辞,总共486首,大部分被收入《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仅《西洲曲》《东飞伯劳歌》《苏小小歌》等不足十首分别归入《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而在《清商曲辞》中它又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部分,前者326首,后者142首,另有《神弦曲》18首。郭茂倩引《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继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又引《古今乐录》曰:“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可见吴声歌出于长江下游建业地区,西曲歌则是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民歌,二者曲调节奏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是情歌。北朝民歌主要形成于五胡十六国至北魏,被收入“梁鼓角横吹曲”,共66首。这样算下来,两部书的民歌总数约为800首,时间上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6世纪,跨越了一千多年,空间上覆盖了中原、塞北到江南的广袤地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美学理想,是中国诗歌的伟大源头。它在时间上早于《号角》一千多年,因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大大地早于德意志。
不同于德国民歌的“散落”以及个人的“收集”,《诗经》和乐府民歌能存留至今,得益于朝廷的“采诗”“献诗”制度。《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牗户而知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国语·周语上》记邵公谏周厉王弭谤时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不悖。”《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周王朝派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利弊盛衰,这就是《诗经》中民歌的由来。当然这些收集来的民歌一定经过了乐官的加工整理,现存《诗经》的四言体、用韵的大体一致以及套句熟语的反复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两汉承继了周王朝的采诗制度,武帝创立“乐府”,专门负责搜集、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创制新声曲调,目的同样是观民俗、查吏治。《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又《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可知乐府的任务是以制乐作歌为主体,采诗入乐,倚调作歌。所用之诗有的采自民间,也有文人的作品。从内容上看,不论“国风”还是两汉及南北朝乐府,都展现了实实在在的人生、社会风情及人间百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