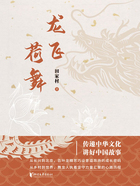
东方苍龙与天平村农民
1949年11月8日,立冬。
此时,早晚的气温已挟带丝丝寒意。这天清晨5点多,下了一场阵雨。阵雨过后,茫茫田野上氤氲着一片白蒙蒙的雾气。这场阵雨并没有影响到庄稼人的心情,因为田里的稻子已经在前些日子被放倒,在谷桶中猛力摔打脱粒,又晒了几个完整的太阳后全部入仓。
家住天平村的王长根睁开了眼,发现窗外已经泛白。他把眼皮子眯成一条细线,本想在床上再烙个饼。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一骨碌起来用冷水洗了把脸,吃下一大碗咸菜泡饭后,抹了一下嘴,起身对堂客(妻子)杜秀珍说:“我约了人要去一趟瞎子老头子家。”杜秀珍看着男人这张严肃的脸微微一笑,然后点点头,她感觉自家男人这几天有点像被龙下了蛊。
这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前天上还是乌云密布,此刻云霞已占据天空,几丝阳光透过稀薄的云层照耀大地。王长根走在小路上,看到一群麻雀从远处飞来,“哗啦”一下落到左边的一块田里觅食,鸟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新中国成立前,王长根家属于赤贫,家里只有三间稻草顶的泥墙房子,吃不饱饭是经常的事。有一天傍晚,暴雨倾盆,狂风像鬼魅那般哇哇大叫,把王长根家三间房子上的稻草全部刮飞了。全家人奋力追出门,跳起来把那些在半空中像乌鸦一般乱飞的稻草捉住,抱在怀里,以减少损失。那时,盖在屋顶上的稻草是很金贵的。
尽管家里穷,但父亲却坚持让王长根这根独苗读到了小学五年级。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当时在村里算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了。王长根不仅是村里的文化人,而且政治觉悟比较高,集体的事他乐意积极参加。
1949年,解放军和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在苏浙皖地区打得天昏地暗。最后,解放军围歼汤恩伯残部7个军8万余人,至4月26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全境宣告解放。解放后,林城镇天平村的百姓欢欣鼓舞,但王长根欢腾的内心却萌生了一个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想法,他要做一件不同凡响的事。
林城镇位于长兴县城以西约15公里处。镇南有一座烟雨朦胧的龙山,镇北有一座青翠叠耸的方山,两山之间,蜿蜒流淌着长兴的母亲河——泗安塘,其丰沛的河水自西向东流经林城,有12公里。
泗安塘流域的南北两侧是平原㘰区,且㘰㘰相连,河塘星罗棋布。世世代代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天平村位于泗安塘南侧,处长兴与安吉交界处的龙山山脉东麓北侧的长泗平原,东连雉城镇,南接安吉县,西依泗安镇,北邻小浦镇。辖沈村、仓里、杨湾、小湾、泥桥、地埔㘰、青姥塘、桥头边、老街、塘埂、㘰角、牌楼等12个自然村,总面积3.68平方公里,粮田面积3180亩,耕地700余亩,水塘287亩。
天平村㘰区内阡陌纵横,河塘交错。生活在㘰区的人,一年的全部收成都指望田里的稻子和塘里的鱼,不像山区,如果田里歉收,还有山上的竹子、笋、茶叶可以指望。种水稻完全是靠天吃饭,逢上大旱的季节,平时能走大船直通湖州的泗安塘也会因缺水见底,河蚌张嘴。所以,大家希望每年都能风调雨顺,田里的庄稼能养活一家人。
据《长兴县志》记载,长兴泗安、林城一带的旱涝灾害曾经非常频繁:
1934年,旱:亢旱成灾,田禾枯槁,长兴第五区泗安各乡为最重,农民秋收绝望,无以为生,遍野哀鸿,嗷嗷待哺。
1944年,旱:大旱,成灾田25.6万亩。
1946年,水灾:7月2日至12日,9月19日至21日,两次大雨成灾,倒塌房屋350间,第一次倒㘰25处,淹没田9.74万亩,第二次倒㘰72处,淹没田12.56万亩。
1953年,旱:6月下旬至8月底连旱70天,西部丘陵地区尤为严重,全县受旱面积14.24万亩,成灾面积12.74万亩,粮食减产1094万公斤。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对农民来说是命,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当地人惧怕干旱,更害怕洪水。曾经,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的百姓以不屈不挠、改造自然的决心,与自然灾害做不懈的抗争,但他们的力量是如此渺小,生活是如此艰辛。
我们的先辈为了读懂天象,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组,每七宿为一组,其中,“东方苍龙”包含的七宿,连起来的形状像一条龙。苍龙七宿的出没与降雨相互对应,所以,先辈认为龙就是掌管着降雨的神,而降雨又决定着农耕收成,农耕的收成则决定着人们的温饱安康,龙便成了农耕社会最主要的“图腾”。
200多年前,在长兴天平和安吉上舍交界处曾经流传过一种“九莲灯”。“九莲灯”又称“花灯龙”,清道光年间,在春节、元宵,庙会或久旱不雨之际,天平村人就会制作花灯龙开展舞龙活动,以感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以前舞龙不单纯是龙的独舞,中间还会穿插多种其他表演形式。王长根还隐约记得,爸爸说这条龙的玄机就是能将一朵朵分开的花,突然变成一条完整的龙。但如何变龙,大家都不清楚。
都说一个人只有衣足饭饱了,才会有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这个说法用在王长根身上肯定站不住脚。尽管生活依然十分贫困,但无法阻挡王长根想做一条龙的想法。“现在解放了,我一定要做一条龙。”他不止一次对堂客说。因为他相信,龙能调风雨,驱鬼魅,能让大家更自信、更团结、更勇敢,让天平老百姓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但王长根从小到大都没有亲眼见过龙的模样,单凭想象,是很难用一双手去还原一条龙的。天平村原来是个大村,有1500多人,因历经战乱,到了1949年,只剩下四五百人。经过打听,龙灯的制作方法只有村上的姚申福、姚申林兄弟两人知道。
王长根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解放那年他31岁,臂粗膀圆的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天早晨的阵雨过后,王长根叫上几个村里的年轻人,兴冲冲来到姚申福家里请教。
姚申福出生于1894年,新中国成立那年他55岁。尽管姚申福的外号叫“瞎子老头子”,但他却有一双雪亮的眼睛和勤劳的手。他是一名木匠,但吹拉弹唱样样在行。后来,他被当地文化部门认定为百叶龙的第一代传人。
姚申福的爸爸和爷爷都曾经是扎龙和舞龙的高手,姚申福和弟弟姚申林小时候给爷爷打过扎龙的下手,所以,这门活兄弟俩并不陌生。姚申林还会扎马灯、花瓶和猴子,这些都是舞龙时的最佳“搭档”。

百叶龙第二代代表性传承人王长根(摄于1980年)
姚申福、姚申林的家也在塘埂自然村,离王长根家只有300米远。兄弟俩的生活条件和王长根差不多,各有三间泥墙茅草屋,不过他们两家的门是木门,比王长根家的竹片子门强一些。王长根见到姚申福、姚申林就直言不讳地说:“申福、申林师傅,我们一早过来就是想向你们拜师学艺,想扎一条龙,表达一下我们翻身得解放的快乐心情。”
由于贫穷、战乱,姚申福、姚申林上一次扎龙、马灯、花瓶和猴子,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解放了,日子太平了,村里的年轻人找上门来,他们有些意外,但很高兴。兄弟俩一高兴,就从屋里拿出几条板凳,让年轻人坐下,在家门口为大家讲起了花龙灯那些风光事。
姚申福不仅手脚勤快,而且也很会说。他说,有一年正月十五庙会,乡里请来了花龙灯队出场表演。那天的表演阵仗特别大,长长的队伍蜿蜒有百来米,一眼看不到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十二月花名”,后面是两匹马、两头牛、一只卖鱼篮、一只卖花篮、两个反穿皮袄举着画眉鸟笼的小丑、一个牵猢狲的扬州美女,还有六只大蝴蝶围花篮,再后面是八个长相俊俏的姑娘举着花灯。当然,马、牛、猴、卖鱼篮、卖花篮都是用竹篾和纸扎的,它们是整个花龙灯表演的一部分。
压轴的花龙灯走在队伍最后,十几个壮小伙把用布包裹的道具举过头顶。里面就是能变龙的荷花,用布包起来是为了装神秘不让大家先看见,这样才能在最后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
他们来到了庙会最热闹的地方,那里已经聚了很多看热闹的人,适合舞龙,舞龙头的队长就指挥12个小伙子分开站成一个大圆圈,相当于划定了一个宽敞的表演场子。
姚申福眉飞色舞地说:“这时,马、牛、猴、卖鱼篮、卖花篮、蝴蝶、花灯先后来到圈子中表演,算是热场,营造气氛,它们有半个多小时的戏份。这些节目都很精彩,特别是举着画眉鸟笼的小丑和扬州美女牵猢狲的表演,又好看又滑稽,一上场就引得观众哈哈大笑,阵阵喝彩。花灯姑娘长得相当水灵俊俏,当她们圆场的时候,场边的小伙子们看得眼睛都直了,还嗷嗷起哄。
“这些节目表演完成后,演员退到四周围成了外圈,花龙灯才揭开了神秘的盖头,呼风唤雨地上了场,舞龙大戏由此正式开始。当然,他们一开始舞的是花,舞到一半才一下子变成龙,看得大家目瞪口呆。这龙就是我爷爷和我爸爸做的,那条龙真漂亮啊,真风光啊!全天下没有第二!”
说到这里,姚申福摇头晃脑,还忍不住抹了一下口水,简直有点自我陶醉了。他的这番描述,把大家听得骑毛驴吃豆包——乐颠馅儿了。
王秋如急急地说:“姚师傅,快教教我们,花龙灯怎么扎?”
姚申福说:“小伙子们,别急,别急,听我慢慢道来。一条龙有舞龙棍子、龙珠、龙头、莲心、龙身和蝙蝠龙尾这几个部分。要用上锯子、铲子、梳子、榔头、画笔、钳子、刨子、剪刀、竹刀、绵白纸、面糊、绳子、洋红洋绿等很多工具材料。以前,我们三个熟练工一起做,也要两个月时间才能做完一条龙。我们扎出来的龙头像个聚宝盆,身体是九朵叠起来的荷花,将荷花拉开就变成了一条龙。说实话,要扎好一条龙很不容易,你们看看,现在很多材料我们都没有,工具也不齐……”
“这么难啊!”有人开始叹息,有点泄气了。
“那我们就看菜吃饭,扎一条简单一点的龙。”王长根是个实在人。
姚申林搭话鼓劲说:“以前有人用稻草扎龙,如果大家不介意,我们可以先扎一条简单的龙试试手,先不要管它好不好看。行不行?”
王长根看看大家,说:“行!万事开头难,只要开始就好办。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先扎一条简单的龙。”
姚申福一挥手说:“好!我们有什么就先用什么,大家一起想办法找材料,找工具。”
大家一商量,就分工领了任务,找材料的找材料,借工具的借工具,还约定三天后的下午一起到王长根家去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