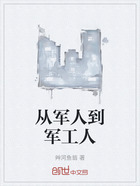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24章 初下连队
1978年4月9日,新兵训练结束。下午,新兵连召开大会,部队给所有的新兵佩戴上了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意味着我们由一位老百姓正式转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会上,宣布了新兵的分配,我被分到了第39师师直属队独立通信营通信连,部队代号为56017部队61分队。
那时我军的直属分队,主要是技术保障部队,一般为营、连编制。第39师直属队下辖有通信营、工兵营、高炮营和警卫连、侦察连、防化连、炮兵指挥连。
4月10日,新兵们分别下到各个连队。通信连全连集合,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仪式后,连队干部带领新兵们参观了挂着多面褪色锦旗的连队荣誉室(兼储藏室),指导员意气风发地介绍连史:通信连于1949年3月第39师在HEN省遂平县城组建时为特务营警通连,解放战争中随军进军大西南到达云南后,驻防于西南边陲的思茅地区(后为PE市)。1955年5月,第39师在原通信分队的基础上组建通信营,通信连为其下辖一连。通信营所属单位还有营部(含修理所、卫生所、汽车班),无线电连(二连),架设连(三连)。1962年,通信营升为独立通信营(副团级单位)。1968年,第13军与第54军换防从云南来到四川后,第39师移防四川内江、泸州、彭县和重庆隆昌等地,通信连随第39师师部驻守内江谢家坝。1975年,第39师由甲种师改为乙种师,通信营架设连(三连)撤销,架设业务并入通信连。
1978年我们新兵下连队时,通信连设有通信排,负责野外传递信息,下设有摩托通信班,装备有长江牌两轮和带跨斗的三轮军用摩托车四辆;骑兵通信班,喂有几匹军马;还有徒步通信班;内勤排负责电话布线和交换机值守,下设有守机班两个,其中一个守机班是清一色的女兵,共10人(野战部队的女军人很少,除师医院和政治部宣传队外,就通信连有一个成建制的女兵班),守机班装备有磁石电话交换机;还有接力班,配置辅助设备载波机。架设排下设三个架线班,每个班6个人,其中班长、副班长各一人。另外连队还有一个炊事班,有炊事员4人,有给养员和饲养员各一人(饲养员的岗位主要工作是喂猪,连队喂有几头大肥猪,每年的春节和八一建军节连队会餐都要杀猪)。每个排只有排长,没设副排长。连队干部基本上是基层专业技术出身,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一个司务长。连部有军械员兼文书、通信员和卫生员各一人。连队的干部战士中,重庆、四川、云南、贵州、江西、广东等南方人较多,也有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山西、安徽等北方人,除汉族外,还有彝、苗、回、藏、布依等少数民族兄弟。
通信连住地在师部大院左侧一个名叫乌龟山的小山岗的半山上,有一溜2米宽的石梯下到师部大院。连队营房是一幢三层的红砖楼房,架设排五班住在三楼的中间。营房前有一块面向山下师部的小平坝,连队每天的早点名、晚点名都在平坝上集合。
平坝当头下石梯处有一棵郁郁葱葱的皂角树,沿皂角树平行有一条通向厕所的石板路。那时,为了改善伙食,每个连队都喂养了肥猪,并在营房周围见缝插针种植了蔬菜,这条石板路大约二十几米,路的尽头就是连队的马厩和饲养猪的棚房,石板路下面的一大片斜坡就是连队的菜地。当兵几年,当过知青的我,经常在山坡上的菜地干过活。
沿石梯往上走几步,营房背后的右面山坡台地,是连队的伙房和食堂。再照直往上走就到了乌龟山的山顶,山顶上有一个篮球场和一个大操场,操场四周是几幢红砖楼房,分别是通信营营部和通信营无线电连。还有防化连、炮兵指挥连的营房以及车库。
乌龟山营区的对面也有一个小山岗,两个山岗之间架有一座小石桥,将营区与内江至椑木镇的公路相连。过了小桥就出了营区,营区外的公路边坡地上是当地农场成片的柑桔林。
谢家坝与NJ市的城区开设有公交班车,途经内江电厂、酒厂、内江东站等车站。士兵外出需要请假后才能出军营,回来后还要销假。师直属队各连队有不少同年入伍的重庆和永川的老乡,只要口袋里津贴没用完,我们星期天经常相约一起到内江城里去购物和游玩。
参观完连队荣誉室后,新兵们集合在连队小会议室进行了分班,我被分到了架设排五班。架线兵是在通信兵这个技术兵种中技术含量不太高但很辛苦的兵种。有老乡为我打抱不平,认为我的新兵班其他人都分到了无线电连,而我却当了架线兵,觉得无线电兵技术性强,工作轻松,环境也好。而架线兵又苦又累又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我的分配很吃亏,但我丝毫没有斤斤计较。梅郁荷德说:“有些人一看见空谷就想到深渊,而另一些人却想到桥梁——我属于后者”。反正我分班后一点都不气馁,我认为架线排这个在通信营最不起眼的集体中反而使我鹤立鸡群,便于我发挥潜能。
分班后,班长带领我们几个新兵搬完行李铺好床,很快就收拾停当,班长交待几句就走了,我站在走廊上打望熟悉环境。有一个老兵听我说一口重庆话,就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绍他是重庆南岸人,去年当兵,现在骑兵班。他乡遇老乡,心里非常高兴,我们亲切地交谈到开饭。
连队的每一间营房住一个班,都睡木板床,一排木柜编了号,每个人都对号存放物品。到部队后,先后给我们发放了崭新的六五式夏装,冬装,军帽,衬衣,衬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被,床单,军大衣,雨衣,解放鞋,袜子,背包带,挎包,口缸,水壶等(其中军大衣和雨衣是旧的,退伍时要上交),这就是一个普通战士的全部家当。由连队保管的武器、弹药、通信器材和战士自己保管的作业工具,战士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在部队,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内务。内务说起来其实都是一些琐碎的事务:墙壁上战士们的军用挎包和水壶要挂成一排,桌子上牙刷方向一致地放在各自的口缸里,地上全班的的脸盆摆放整齐,这些要求有点类似于工厂的定置管理。整理内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把被子叠得四楞四线,俗称“叠豆腐块”。叠被子挺费神,新军被很厚,叠起来形如面包酷似花卷,我用脚踩用膝盖跪用肘压用手捏,想尽一切办法,但要把被子整的有楞有角谈何容易。
我武断的认为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要求莫名其妙,在叠被子上下功夫没得必要,纯粹是耽搁时间,浪费精力。心头不免不耐烦,嫌麻烦,马马虎虎应付了事。结果连队第一次内务检查中,我叠得松松垮垮的被子根本不是一块“豆腐块”,而是一个“大馒头”,扯了全班的后腿。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还在晚上的班务会上拒不接受批评。老兵们纷纷给我“上课”:内务条例中的“整齐划一”是部队“抓作风养成”的手段,是培养组织性的基本要求,要引起重视,要服从规定。
道理是这样的,可我却不甚了然,居然像在读书时当学生干部一样装酷摆谱,口吐狂言,说些啥子“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云云。开始战友们听我这个新兵蛋子开黄腔打胡乱说,便耐心地给我讲道理,讲纪律。自视甚高的我充耳不闻,还嫌他们啰嗦,时不时的顶嘴狡辩,语音里含有明显的抵触情绪。
就在七嘴八舌之间,不善言辞的我没有把握好语感,漫不经心一句“没得耍事得”冒犯了班长,惹恼了众人。
“这是什么话?”班长气得七窍生烟,他声色俱厉,咆哮如雷,“你娃才来几天,有什么资格对部队的规矩说三道四?”
当时的情景应了一句重庆言子“非洲老头跳高——黑(骇)老子一跳”。十几岁的我哪里见过这种阵仗,明白自己遇到麻烦了,一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赶紧拿出妥协的姿态,胆战心惊地摸出一支香烟,诚惶诚恐的递过去。
哪知班长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阴沉着脸,粗鲁地一把推开我的手。平时彬彬有礼的这位兄长,敲着桌子忿忿道:“城市兵扯淡”。
我耷拉着脑袋,心说至于吗?难免心生芥蒂,埋怨班长“小题大作”。但嘴巴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在心头黯然地骂了几句“宝器”泄愤。
转眼到了下连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到部队后被关在军营一个月的新兵们,得到了自由上街进城的机会。早饭后,我背上部队发的草绿色单肩斜挎包,和几个老乡急不可耐的去请假,打算到NJ市区购物游玩。哪知班长脸色一沉,十分难看,好说歹说就是不批准我请假。不准我上街也就算了,他还故意派我到炊事班帮了一天厨。
看到兴高采烈的战友们身穿新军装,纷纷相约出了军营,兴冲冲的我气得捶胸跺足。我还误解班长派我出公差,是对我自由散漫的处罚呢。但我不敢违抗命令,悻悻地到炊事班打杂帮忙去了。
本来出个公差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但它让年少轻狂的我初步认识到部队铁的纪律不是闹着玩的,也领教了作为部队兵头将尾的这个老班长的厉害。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知道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知道部队的铁律:服从是无条件、是不讲价钱的。也搞懂了“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我终于明白了“管理出战斗力”的道理。用重庆言子来形容,就是晓得了“锅儿是铁铸的”。
我再也不敢造次,不敢拿全班的荣誉当儿戏了,对班长的成见也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星期一我起了一个大早,规规矩矩把棉被摊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琢磨了半天。
一旦用了心,脑筋很快就开了窍。我这人大本事点都没得,耍点小聪明倒是轻车熟路。我按老兵教的方法,端起口缸喝口凉开水,像喷雾器一样喷到被子叠好后的正面上,然后使劲压,这样反复几次,终于把它叠成了四四方方、楞角分明的“豆腐块”。
利用早饭后的空隙,我忐忑不安的请来班长验收,争取关系转圜的契机。果然,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的老兵,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看不出你娃“板眼还多吔”。紧张得满头大汗的我,见班长认可了我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悄悄松了一口气,这事就戏剧性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刚下连队那段时间,每天早晨师部大院的广播里起床号一响,大家便要翻身起床,只有一刻钟的时间穿衣叠被上厕所。有时动作稍慢或遇到厕所打挤,来回就要小跑,才能赶上集合出早操。
半个小时的早操后,大家抓紧时间洗漱。吃饭前全连先列队唱歌,再听口令一个班一个班排队进入食堂,拿自己的搪瓷碗打饭菜,又以班为单位围坐一个方木桌就餐。半个小时的开饭时间不允许讲话,大家静静地埋着头专心吃饭,一般都是提前吃完。
早饭后是器械训练,或队列训练,或射击、投弹训练。中饭后,或训练或安排学习。
我们连负责营区小桥边哨位的站哨任务,各班轮换站哨,站一班哨两小时,24小时不间断。晚上换哨开始是班长叫醒,后来就是哨兵自己回来叫醒。
师部每周六都要在师部大礼堂组织放电影,每场电影前师直属队各单位在指定的位置坐好后,都要相互拉歌。常唱不衰的军旅歌曲《我是一个兵》《说打就打》《打靶归来》,或者语录歌《下定决心》等等,口气冲、节奏快,调子硬邦邦的,唱起来非常畅快。
拉歌不比谁的歌唱得好,比的是谁嗓门大。一般由指导员或副指导员站出来手舞足蹈,指挥全连战士挑战其它连队。宽敞明亮的大礼堂里,雄浑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掌声和吼叫声响成一片,很是热闹。那排山倒海的气势,展示了革命军人的精神风貌。
生性腼腆的我,也由开初斯斯文文的小声附和,到后来扯开喉咙把声音融入那山呼海啸般的军歌大合唱。在酣畅淋漓吼叫中,平时的扭捏之态一扫而空。
从下连队开始就按月领取津贴。当时的义务兵津贴是逐年增加的:第一年每月5元、第二年每月6元、第三年每月8元、第四年每月10元、第五年每月15元、第六年每月20元……。
一般来说,能挣钱是一种能力,会花钱也是一种能力。那时当兵的哪有这种能力呀:有的兵舍不得用,存起来。虽然津贴不多,但因为部队实行供给制,服役几年居然存了好几百;但大多数人每个月津贴领取到手,就到军人服务社或星期天上街去花个精光。我属于后一种人。
那时,部队干部战士同吃同住,战士拿津贴,吃穿用全都由部队供给,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干部拿工资(排级干部多为行政23级,每月工资52元;连级干部一般为行政22级,每月工资60元……),干部的军大衣、内衣等要自己花钱买,每月还要交伙食费(与战士的伙食标准相同)。
当时驻川陆军部队的伙食费是每天人均四角六,在承担国防施工任务期间则再补贴一角。军营里的伙食,比起传统的大锅饭另有特色,菜品虽说不上精美,谈不上色香味俱全。但菜的分量充足,饭随便吃管饱。只是那时的条件还不足以维持每天一顿肉,所以连队实行的是每周打两次牙祭。三餐之外,有时因为晚上安排夜间训练或执行施工任务,回营后需要加餐,则由炊事班下面条。
军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必须进行高强度的训练,还要经常接受抢险救灾、国防施工等艰巨险难任务,能量消耗巨大,每天只要饭点时间一到,值日干部便吹哨集合队伍,大家唱着嘹亮的军歌,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食堂门前坝子列队,依次进入热气腾腾的食堂内,在炊事班窗口排队打菜,米饭或面食自取,然后以班为单位围在一起吃饭。
我们部队驻防南方的四川,以大米为主食。部队的北方籍战士多习惯面食,有次向连队提出希望打牙祭时吃顿饺子。由于连队南方兵居多,北方兵较少,加上这包饺子是个技术活,困难不少。但为了增强团结,满足战士的愿望,我当兵那几年连队也组织过两次包饺子打牙祭。
为什么还要组织呢?是因为炊事班几个人要包全连百余人的饺子确实忙不过来,所以炊事班只负责加工好馅,然后各班到炊事班领回面和馅,发动全体战士自己动手包。南方兵不会包不要紧,由各班北方兵手把手教。
包饺子主要的困难是没有专用工具,由大家自己想办法解决。于是和面、擀面各显神通,有的班以桌子为案板来和面,也有以床板为案板的(先清洗干净);有的班以铁锹把凑合当擀面杖(每个班都配发有十字镐和铁锹,找块碎玻璃把手把刮光滑就行了),擀的皮大小不等、厚薄不一。有个从来没有包过饺子的南方兵,干脆将面擀成一张大薄饼,然后用口缸扣出一个个饺子皮,这个发明创造很快得到其它班的响应。
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大家包出来的饺子五花八门,两头尖的,两头圆的,一头尖一头圆的,没有褶子的,反正什么形状都有。各班完成任务后,送回炊事班下锅煮熟,煮烂的煮散的不计其数,但大家依然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
在部队,每年的春节和八一建军节,是两个主要的节日,部队都要放假,连队还要杀猪聚餐(以自己喂养的猪和自己种的菜为主)。聚餐前一天开始,各班都要抽人帮厨,聚餐时可以喝酒(平时不准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