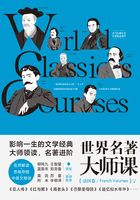
第四节 与野心相比,爱情永远位居其次
《红与黑》是法国小说,甚至是世界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在18世纪,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出现之前,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流行的都是书信体小说。
第一,书信体小说的特点是一封信接一封信,有时联系十分紧密,但多少有一种内容被打断了的感觉。从这封信到另外一封信,间隔可能不止一两天,也可能是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所以时间不是完全紧接的。第二,书信体小说表露了写信人的心理状态,但这种心理状态并不是心理描写,二者是有区别的。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到19世纪初,书信体小说基本上就变了。
斯丹达尔的小说是将人物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主人公的一生为主线,并把主人公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彼此结合,从头写到尾。大家可以看到,《红与黑》的场景先是小城维立叶尔,然后转到贝尚松神学院,再转到巴黎。这里可以看到16世纪中叶的流浪汉小说的痕迹,但是它已经不完全是流浪汉小说了,它瞄准的是人物一生的经历。
主人公的性格很鲜明,其他人物也各有特色,比如说《红与黑》里的德·雷纳尔夫人,玛蒂尔德小姐,还包括市长、侯爵等,都各有各的性格,但他们都依附于主人公。这样的写法,应该说从斯丹达尔开始的那一批作家已经有意识地使用了。比如巴尔扎克,他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基本上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后来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一些小说了。这种结构标志着法国的长篇小说已经达到现代小说的成熟阶段了,由此诞生了一大批名家,出现了一大批经典作品。
我觉得这种写法应该是从斯丹达尔开始的,当然,可能当时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这种结构的独到之处。而且这部小说出来以后,是不是那么受欢迎呢?也不是。因为斯丹达尔是超前的、引领了那个时代的。《红与黑》刚出版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反而遭到了一些作者和批评家的贬斥,比如批评家圣伯夫。
提到圣伯夫,我还要多说几句。圣伯夫虽然可以称为19世纪法国最出色的批评家之一,但我认为普鲁斯特对他的批评是很正确的,普鲁斯特认为他根本就没有推荐过19世纪的大作家,无论是斯丹达尔、巴尔扎克,还是福楼拜,他一个也看不上。他看上了谁呢?是以前的一些作家,那他这样怎么能算是一个大批评家呢?他不是批评作家的作品,而是“批评”作家的生平。圣伯夫用生平来印证作家的作品,这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圣伯夫认为,小说人物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精巧的木头人,这个评价也是很令人惊讶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重视斯丹达尔的这部作品,但歌德注意到了。歌德在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到《红与黑》,歌德认为这是斯丹达尔最好的作品,但他同时也觉得这部小说的女性角色的传奇色彩过重,不过这抹杀不了作者杰出的观察精神和在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可以看出,歌德还是很有见地的。
泰纳在19世纪下半叶,曾试图为斯丹达尔的作品正名,而斯丹达尔本人始终是满怀信心的。斯丹达尔曾说,“到1880年,将有人读我的作品”。果然,在19世纪下半叶,《红与黑》受到了绝大多数批评家的赞扬。
说实话,《红与黑》这部小说的简洁风格,并不为所有的翻译家所理解。我国的一些有名的翻译家也不理解斯丹达尔的简洁,他们选择用华丽的辞藻来翻译《红与黑》。比如,《红与黑》的最后一句话的主体是Elle Mourut,指的是德·雷纳尔夫人死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有的翻译家怎么翻译呢?“她魂归离恨天。”那就奇怪了,斯丹达尔怎么可能知道“离恨天”?“离恨天”是中国古代的说法,翻译成“魂归离恨天”读起来很美,但其实违背了斯丹达尔简洁的写法。
“她死了”是最恰当的一种译法,语言看似很简单,但正是《红与黑》的特点。另外,我认为翻译《红与黑》这部小说,需要力求简洁,但简洁不等于平淡无味。而且虽说风格简洁,但有时小说中句子的语法结构还是很复杂的。有的翻译家把这部分句子翻译成了比较复杂的欧化式句子,这也是可以的。
20世纪90年代,我国曾经出现过一场关于《红与黑》翻译问题的大讨论与大评选。专家教授也好,退休工人也好,都参与其中。评选结果是,获得第一名的译本中有很多的欧化句子,而讲究词汇的却排在最后,尽管他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读者不承认,读者认为按照讲究词汇的译法翻译的译本用语很做作。
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也就注意两个方面。前面提到过,简洁不等于平淡无奇。没有一点文采的翻译是不成功的;文采的问题要注意,但是也不能译出太多的欧化句子——有一些欧化句子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但不要太多。因此我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将这两方面调和,展现小说的本意。
《红与黑》这部小说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长篇作品。尽管这部小说谈的是较远的历史,离现在已经差不多两百年了,但是小说所描写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还是很吸引我们的。
《红与黑》的那种现代思想,以及对男女爱情的写法还是很吸引人的。尽管这是一个关于野心家的故事,其中的爱情片段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却很能吸引读者,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的道德观念去评价于连,如果用今天的道德观念评价,也是讲不通的。于连是很特殊的一个人物,他的经历也有值得人们同情的地方。
这部小说我不是一口气译完的,20世纪90年代我译了一半,后来停下来了,因为出版计划取消了。退休后,我又把它捡起来,继续翻译。因为法国的作品太多了,我的翻译选书标准就是法国的经典作品,而且经典作品我也只是翻译一部分,比如巴尔扎克那么多的经典,我译不过来。
当代小说,我译得也比较少。因为我觉得当代小说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历史对它如何评价还不清楚。今天有人认可它,可能过了50年,评价就不一样了。但是有的书,比如雨果的作品,就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的,而且他的小说不是很多,同时就我个人而言,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我就想到翻译雨果的小说。他的几部重要的小说,我以前都译过,比如《悲惨世界》《九三年》《海上劳工》《笑面人》等。雨果其余的作品中有两部是从来没有被译成汉语的,现在我也把它译过来了,准备出《雨果小说全集》。
阅读小说时很多东西是我们普通读者不理解、不清楚的。比如说读法国小说时,我不了解这个作者是什么情况,就想要看一看译者写的序言。因为我是做研究的,有这个基础,所以对我翻译的小说我都写了比较详细的序言,当你看了序言以后,你就会对这部小说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有进一步的理解。有些翻译家是不写序的,他们认为写序太容易了。其实他们写的序,如果只是对作者生平、对小说内容的简单介绍,我认为是不够的。
《红与黑》有那么多内容,不是一般的读者能理解的,那让我们了解一下不是很好吗?比如政治方面,作者写到了阴谋,我们了解吗?读了序言后,才会明白,原来是这样的,斯丹达尔还写了这么重要的内容!
又比如心理描写,我们看上去好像挺好玩的,但并不知道心理描写的特点以及魅力所在。这个时候译者做些介绍,读者才能更了解。
我们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是需要去读一读序言,不光是我翻译的版本有序言,别的译者的译本也有序言,都可以读一读,这样可以加深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艺术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