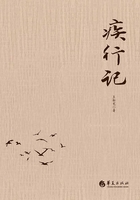
“君子之交”同志情
厂里的事说了不少,该说说公司的事情了。
民政工业公司所在地是广州起义路162号址,说起来这里还有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该路开辟于1919年,当时起名维新路,寓意要走推翻清朝、维新变革之路。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两个月,在这条路叫素波巷的胡同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1927年我党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成立的新生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就设在维新路国民政府“省会公安局”里,位置就在从公司往北走约300米处。1966年,老马路改名为“广州起义路”后一直沿用至今。
话回到1984年年初,公司党委召开公司领导干部民主推荐会议,会场在首层旧礼堂,屋顶是圆木金字架的大梁,地面是老式的大方块红地砖,两旁的窗户让邻家墙遮挡了,阳光难以自然照射进来。
会议由公司党委主持,各厂副职以上的干部全部参加,陈汉书记做动员讲话。我还依稀记得他在会上说,希望大家从民政工业的长远发展考虑,推荐出有事业心、有基层工作经验、年富力强的同志。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同志,已经记不起名字了,他微微笑看着我说:“哟,说的条件好像和你都能对上号啊?”说实话,当年公司系统有四千多号职工,这队伍里包括一批资历丰富的“老民政”干部,所以,我压根儿也没往那方面去想,更没有得到过其他什么信息。
不久,经过一系列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程序,我被市民政局党委任命为民政工业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这时候算下来,我已经在福利企业工作了14个年头。当时,对组织的职务安排,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感到的压力是自工作后从没有过的。在厂的欢送会上,厂领导、厂部办公室和各车间负责人都参加了,大家相互紧靠着围坐成一圈。我眼前都是相处了十几个春秋的同事,平日见面熟视无睹,甚至还发生过言语争执,说真的要离开了,大家不由触景生情,有的同志眼睛湿润了。
黎彭坐在我身旁,他觉察到我的思想负担挺重的,语气关切地说:“阿新宪,以你的能力,我觉得完全可以胜任,不要紧,不用顾虑太多啦。”要知道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及时的信任和鼓励,还真是难得啊。何况我一下子从老黎的下级变成了上级,他依然对我这么真诚坦荡,这更是难得了。听了这番话,我绷着的大脑似乎松开了紧箍咒,思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1985年下半年,黎彭调海珠区任民政局副局长。这期间,又遇上一件很巧的事情:我与老黎分别代表市和区的两方,共同处理移交海珠区瓶盖厂(福利企业)资产的事宜。工业公司是移交方,海珠区民政局是接收方,具体办事的同志各为其主,出于为本单位多争取些利益的动机,连厂里办公电话的归属也争执不下。我主动与老黎商量后,向郑国帆经理建议:区里的情况比较困难,做一些让步有利于照顾下面的工作。最后经多次友好协商,大家都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厂领导黎彭、张善林(三排右五、右六)等与部分干部职工合影(1984年9月)
岁月的流逝,没有冲淡我们之间的感情。黎彭后来办了辞职,全家移居到美国。他回国探亲时我俩在越秀天安大厦喝茶,他缓缓地回忆道:过罗湖桥的时候,我真是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两个孩子能出去念书,还是违心过了界桥。他还告诉我初到美国那阵子,为了挣钱交房租,他每天都要爬上三米多高的梯子,给当地人粉刷墙壁,要干满整整两周才能挣到一个月的房租。后来,又在华人开的小杂货铺当搬运工、收银员。听了老黎这番苦涩的叙说,我真不知道该鼓励呢还是安慰,只是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这时讲啥都是多余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如今,许多老领导、老同志已经走了,但在我脑中他们从未远去:吴庭芳、卓仁道、周杜南、谭锡华、李夫、宋仲霖、陈汉、郑国帆、张定平、李雄、关世良……
思之得
与同事关系相比,处理家庭关系有时要困难得多。血亲、姻亲的“粘连”,使后者的“重要性”排列在了前头。不少干部大半生清醒明白、睿智过人,最后还是倒在亲属熬制的“温情汤”里。快乐、幸福又夹杂着痛苦、无奈,可能就来自世俗家庭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