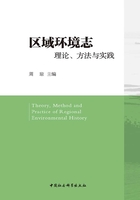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五 余论
环境史需要关注特定区域人群的生活场域,这种历史场域的复原,要对特定区域内特定人群生计方式、民俗习惯、行为方式等问题进行关照和挖掘。特定区域的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的人群属性,环境史研究应该将这种具有本地人群属性的环境变迁过程揭示出来。环境志即可以实现此目的,让参与环境的主体人群表达其所感知到的环境演变历史,从而推动环境史学 “向下”发展。
从方法论上看,环境志在史料选择与运用上并非对传统文献的抛弃与割舍,而是在传统史料文献的梳理、解读基础上,运用口述资料将传统史料中重要的关节点串联起来,同时也为开展更精细的环境演变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在具体开展环境志研究过程中,合格的口述访谈对象具有敏感的地方乡土知识与地方经验,这些细微知识为实现立体呈现环境变迁有积极作用。此外,口述访谈对于复原历史时期人类作用自然的关键技术有极大价值,可以帮助解析影响环境变化的内在驱动因素,以及技术消失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
笔者认为,作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阶段或新方法,环境志在转变传统环境史学研究中的主客体,以及揭示环境变化后的人群心态转变上具有显著价值。传统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古代环境史研究,基本没有专门涉及环境、生态的史料,要研究环境变迁,所用史料多夹杂在其他专题文献之中,进入近代以来依旧如此。如学者在关注灾荒影响过程中,会分析灾荒形成的环境背景、生态效应等,环境就会被涉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没有形成专门的环境保护志书,70年代以后虽有了部分专门的环保志,改变了“环境”在文献资料中缺位的现象,但环保志以揭示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保护过程为主,强调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预防环境恶化、控制环境污染,这与目前对环境高度重视的社会期望仍然有差距,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有更细致、深入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作参照。
最后,通过口述访谈形式开展环境史研究,笔者还希望揭示生境突变对区域人群的生计影响,以及由此而在当地人心理上留下的印迹,关注环境变迁对人群心态的影响。这也是环境志区别于传统环境史研究的最大不同之处。
[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20世纪云南水田演变与生态景观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CZS06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耿金(1987— ),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环境史、水利史、农业历史地理。
[2] 赵九洲、马斗成:《深入细部:中国微观环境史研究论纲》,《史林》2017年第4期。
[3] 朱志敏:《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 杨祥银:《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曹辛穗:《口述史的应用价值、工作规范及采访程序之讨论》,《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4期;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5] 左玉河:《中国口述史研究现状与口述历史学科建设》,《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6] 如周琼对历史时期瘴气演变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田野调查中,通过对当地老人口述访谈的形式揭示瘴气存在以及消亡过程[周琼:《寻找瘴气之路》(上),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寻找瘴气之路》(下),载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文田野》(第2辑),巴蜀书社2008年版]。此外,张玉洁基于环渤海渔民口述访谈而开展的海洋环境变迁研究(《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环渤海20位渔民口述史》,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海洋大学,2014年),郑玉珍以口述史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渤海海洋环境变迁状况(《捕捞渔民对海洋环境变迁的主观感受——青岛市S区渔民口述史》,《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3期);而在历史建筑的保护中,也借助口述史方法,复原古建筑周边的“环境”(蒲仪军:《陕西伊斯兰建筑鹿龄寺及周边环境再生研究——从口述史开始》,《华中建筑》2013年第5期)。
[7]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洱源县河湖专志集》,云南省新闻版局1995年版。
[9] 杨煜达:《中小流域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清代云南弥苴河流域水患考述》,载曹树基《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3页。
[10] 又名大理裂腹鱼(学名:Schizothorax Taliensis Regan),属鲤科裂腹鱼亚科,裂腹鱼属,喜欢生活在静水环境的中上层,食物以浮游生物为主。产卵时要求流水环境,每年4—5月繁殖季节溯水上游到沙砾河床的河流或湖底地下水出口处产卵。卵需在流水中孵化,当地渔民利用弓鱼溯河产卵习性,在河口设竹箔拦捕(黄开银:《大理裂腹鱼及其繁殖保护》,《科学养鱼》1996年第1期)。在历史文献中,“弓鱼”又称“公鱼”“工鱼”,对于名称辨别本文暂不作考辨,民国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有过辨析。
[11] 洱源县水利电力局编:《洱源县河湖专志集》,云南省新闻出版局1995年版第109页。
[12] 咸丰《邓川州志》卷4《物产》,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3页。
[13] 咸丰《邓川州志》卷首《河工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9—15页。
[14]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80页。
[15] 管彦波、李风林:《西南民族乡土传统中的水文生态知识》,《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16] 段子飞,1965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9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打鱼行业。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
[17] 段镇王,1944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
[18] 张炳胜主讲,段镇王补充说明。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张炳胜,1968年生,大理市上关镇河尾村村民,在上关镇从事水务管理工作。
[19] (民国)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20] 杨耕:《“人的问题”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5期。
[21] 咸丰《邓川州志》卷4《物产》,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3页。
[22] (民国)陆鼎恒:《洱海的工鱼》,《西南边疆》1940年第8期。
[23] 段镇王主讲,张炳胜补充说明。访谈时间:2018年8月19日,访谈地点:河尾村耆英会。
[24] 褚新洛等编著:《云南鱼类志》(上),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