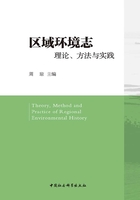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三 地方经验:乡土知识中的环境逻辑
环境志研究需要挖掘基层人群的乡土知识,这种知识是当地人群与环境互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地方经验(Local Experience)。管彦波、李凤林指出:“乡土知识是各民族在长期生存与生活实践中,围绕着与生境资源的关系而构建的一种比较完备的环境认知体系,其本身是一种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论。” [15]这种乡土知识是特定人群对周围小环境的认知,是当地人群长久积累的集体经验,具有潜在的生态价值。
笔者在洱海北部的田野调查中,关注弓鱼消失过程,并试图探讨其对当地百姓生计带来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弓鱼就基本灭绝了,在当地的走访中,1960年后出生者已经很少见过大量弓鱼,1950年后的也有不少人能描述一部分弓鱼生长情况,而主要的经历者以1940年后人群为主。随着这些见证者的逐渐逝去,对历史时期弓鱼生境的认知,及渔沟这种具有复合生态价值的历史遗迹,也随着新环境对人群塑造与影响而消失。而环境志就希望“复原”这种历史上存在过的人与环境共生状态。对于弓鱼消失原因,有些文章中提到与银鱼引进有关。但从与当地90年代最先开始捕银鱼的村民访谈中,厘清了弓鱼与银鱼之间的逻辑关系,“银鱼的繁殖能力很强,到1991年我就开始捕捞银鱼了。这种鱼当时老百姓不叫为银鱼,称玻璃鱼。这种称呼在当地,那个时间段的渔民都知道。银鱼含高蛋白,到一定季节就自然死亡,死亡后沉入水底,腐烂后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越干净的地方银鱼越多,整个洱海里的数量非常多。”[16]段子飞是第一批开始在洱海里打银鱼的渔民,称洱海里引进银鱼是在1990年左右,此时弓鱼早已灭绝,因此弓鱼与银鱼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是,弓鱼最终灭绝可能与其他物种的引进有关:“弓鱼的消亡,可能还跟弥苴河中的虾、小花鱼繁殖有关。弓鱼产卵在沙地、沙滩上,小虾、小鱼就把鱼子吃掉了。这些虾和小花鱼都是外来物种。”[17]在70年代后期弥苴河下游还有弓鱼,但是量已经比较少了,为了弥补弓鱼减少对当地生计造成的冲击,于是从外地引来了一些鱼虾,可能最终导致弓鱼消失。
此外,一些乡土现象一般也很少进入文本材料中,而通过口述访谈获得的这些信息却是极佳的研究素材。渔沟形成之初是为分泄弥苴河主干河道洪水,并灌溉农田,鱼类资源为其附属产物,因此,渔沟排水不畅就会出现下游河道溃决、淹没农田现象。当地人提及,在上下游河道工程系统整治前,弥苴河下游沿岸的农田在水稻收割季节经常出现江水漫灌现象,“过去经常会有撑船割稻谷,原因是部分年份洱海水位高,或田相对较低,缺少排涝沟渠。水稻成熟期过了不收割,会发芽,一定要抢收,即使是农田里积有大片的水,也要收割。在本地,水稻的秸秆用来喂牛。如果水稻被淹的时间过长,秸秆就不能再用于喂牛。”这种“渔沟”排水不畅而形成的灾害生态及农民的应对反应,很少在传统文献中出现。此外,当地对于田间的排涝沟渠也有专门的名称,具有生动的生态知识与环境信息:“水沟在本地有几种名称,取水口在弥苴河的为渔沟,在田间排水的沟渠称排涝沟,本地人称黑泥沟,因常年淤积,土质成黑色。” [18]当地还有一种引水沟渠,称龙洞,陆鼎恒在当地调查中记载了这种水利设施:“还有若干由湖滨向内开的半截沟,并不通到弥苴河,则名叫龙洞,以捕杂类小鱼。”[19]这里“龙洞”与“渔沟”并列,渔沟与弥苴河相通,而龙洞则只与洱海相通。在走访过程中,村民带笔者查勘了各种龙洞,然现存的龙洞却与弥苴河直接相通,和清至民国时期文献里记载的有极大差别了。其作用主要是将水引进村子,并进入农田。龙洞引水水口很窄,靠钢制的水闸控制水流,在干旱少水时节,则要依靠水泵提水引入龙洞。相比于“渔沟”的退出,龙洞在当地仍在发挥作用。
这些基层生态的细微转变过程,以及其间的逻辑关系,需要在口述访谈过程中不断收集、整理,这不仅是出于本体研究的需要,也可以为从事相关研究保存史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志本身也是一种文献收集、保护的手段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