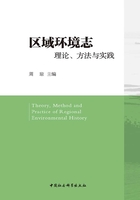
二 环境志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如果我们已经模糊地梳理出了环境志的轮廓,它将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此为基础,推展为三个部分:具体环境问题、个人环境记忆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
环境志首先可以研究某个具体的环境问题。口述调查与传统的资料收集方法相比更强调对个人记忆的收集,如果把这种收集方式用于调查有相似工作或生活经历的某一群体,只要调查内容清晰、方法设计得当,便可以还原某个被传统记录忽视的环境问题,从而产生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现在的一些经验来看,环境志研究中的口述史可以调查一场自然灾害,也可以调查一场瘟疫,或者一种历史上的特殊疾病及一个特定区域的环境变迁史。在口述史和环境史探索的前沿已经出现了一批可以归入此类的调查,且大多集中在对环境变迁状况的研究中,如程林盛对湘西苗疆环境变迁的口述调查[13],以及崔凤、张玉洁对环渤海环境状况的研究[14]等便属于此类。一些研究已经有意识地将环和境口述两个要素进行有机结合,比如罗尼·约翰斯顿(Ronnie Johnston)和阿瑟·麦克弗(Arthur Mclvor)通过调查苏格兰克莱德地区工业发展与职业病患者,重现二十世纪中期清洁空气法案实施之前的环境污染状况的尝试[15]。在文章的前两个部分中,他们先是通过大量文献调查和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梳理,还原了兰克莱德工业发展的基本状况,而在之后的工人与工作环境部分,则开始大量运用口述调查材料,由此得以生动地整理出在这种环境背景下的人类生存状态。尽管整体论述方式与传统研究无异,但正因为有口述材料的帮助,他们才能够更好地呈现研究对象所在时代的环境情况。
环境志也可以研究人物。口述历史发展的基础就是对个人记忆的总结和归纳,本就适合进行人物研究,因此环境口述史在对个人的环境信息研究中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如波特利所说:“如果说口述史有什么不同,就是它向我们讲述事件的意义大于事件本身。”[16]在利用口述方法探讨人类的环境感知部分时,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人物陈述的历史内容,更要关注这些陈述者自身的表达和感受。具体调查实践中的个体感受,又可以细化为两个方向:一是围绕某个问题对个人感受进行收集和整理。研究者可以将环境事件与心理学方法结合以便深化,如鲁斯·莱恩(Ruth Lane)关于个人科学知识对认知环境变迁的研究[17]。在对澳大利亚蒂默特区域(Tumut Region)的环境状况分析中,莱恩独辟蹊径从土地开发者对科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入手,分析一些不良土地管理决策的产生原因。他的研究虽是围绕着环境问题展开的,但却大量融入了对个体心理认知、思想解析和行为模式等相关分析手法。这种访谈调研,可以探索受访者的思想领域,将个体认知与主观行为结合,从某种角度亦可证明,环境口述研究具有将人类思想与改造自然的方式更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的潜力。
除此之外,环境志也可以用于分析环境史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与普通口述访谈不同,从环境志视角出发的研究,不仅可以搜集整理环境史研究者的个人思想和生活发展经验,为后世学者留下参考,还能够把这些个人信息进行组合分析,梳理出某个时代环境史学的发展路径。丹尼勒·恩特雷斯(Danielle Endres)在环境交流和公共史学研究领域做出过类似的实践[18],他在传统研究中融入口述史学方法,以便于了解复杂的个人经验,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及探寻表面现象的深层因素。总体而言,恩特雷斯的研究思路是对参与者群体的认可,他认为如果研究一场环境运动应该辅以采访组织者和参与者,研究一些环境问题应该访问与之相关的科学工作者,如果扩展这种思路,那么对环境史的研究同样需要对环境史研究者和参与者展开访谈。在环境志研究中,环境史的研究者和参与者们同样也是宝贵的研究对象。
此类环境志研究必然会为环境史学史提供更鲜活的素材,甚至在具体信息的搜集整理中,还可能在环境教育、环境认知及自然或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视角,出现让我们意外的启迪和收获。
环境志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是地域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环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环境史学家们在探寻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传统文献不足以(或不能及时、全面)阐释调研事件的情况。为了弥补这些缺失,一些研究开始在实践工作中融入社会、人类学或结合其他学科的综合调查方法,并强调亲临其境展开研究。2009年2月澳大利亚发生一场破坏性很强的森林大火,灾难过后澳大利亚政府组织各类科学家建立考察队,深入林区了解灾情并着手制定复原方案。一队由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环境史学家组成的队伍也参加了对这场大火的实地研究,其中也有一名环境史学家——汤姆·葛瑞芬斯(Tom Griffiths)。葛瑞芬斯在他随后写成的颇具影响力的作品《灰烬之林:一段环境史》[19]中生动地刻画了此次对灾区和灾民的考察。实地考察也让他对森林状况、开发管理手段等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并帮助他得出结论,即在这片森林自身的生态系统中,不时发生的山火本是这片森林生态系统的一环,欧洲人的到来虽然改造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但不能改变森林生态系统。调查和随后的研究成果揭开了人类与自己聚居地之间的深层关系,也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比如2015年凯蒂·霍姆斯(Katie Holmes)和海瑟·古德奥(Heather Goodall)组织的实地调查项目,便是直接受到葛瑞芬斯著作的启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拓展了对田野调查、口述访谈以及人地关系等问题的探索,他们的努力让口述更好地与环境史研究融合,也更关注地域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地域与人之间关系的环境志,能够产生各有特色的个案研究,提供呈现人地关系变化的典型案例。利用口述方法对作为个体的自然改造参与者的思想进行分析,能够更深入地分析人与聚居地(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说,这种研究视角也必将成为环境志重点考察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