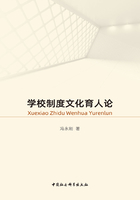
导论
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谈人生》
学校是进德修业的专门机构。学校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以培养人才为己任,是“以文育人”“以文砺人”“以文化人”的专门教育机构。究其存在与表现形式而言,学校并非自然而生,而是教育制度化、形式化教育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学校所具有的存继、传播、交流与创新文化的功用,以及学校所肩负的育人职责,将制度、文化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学校制度、学校制度文化、学校道德教育及其关系由此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这种内在关联,不仅使学校的育人活动无法也不可能脱离制度文化的保障和引领,而且勾勒出学校制度文化和育人活动所具有的合作联动机制与共生效应,将二者紧密地衔接起来。
一
重视育人工作是我国学校教育的悠久传统。自学校产生以来,对学校文化育人功能的探讨一直是研究者的不懈追求和努力方向。孟子首次提出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的道德伦常教育。“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育人标准和育人要求。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尤为重视道德教育,并将其与选官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无论是汉朝的“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始自隋唐直至清末的“科举制”等人才选拔制度,均注重对考生的“孝”“悌”“仁”“义”“勇”等内容的考查,均把道德及道德教育放在了突出地位。即使是在明清时期,科举制日益腐朽和没落,但出题范围仍然集中于人伦道德范畴。尽管我国古代社会的学校育人活动具有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但积累的一些精华如上善若水、诲人不倦、理想人格、立志笃行、知行合一等,对于今天依旧有巨大的借鉴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党和国家不遗余力地强调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各级各类学校也在全面加强道德教育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安排与部署,取得的成绩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暴露出种种隐忧。对此,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指出,尽管我们如此关注学校道德教育,但效果却不尽人意,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当前学校教育中最令人担忧、令人棘手的恰恰也是学校的育人工作。造成这种窘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学校外部的因素,如全球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和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等的冲击,也有学校内部的原因,如思想认识不到位、贯彻落实不得力、激励机制不健全、保障体系不完善等的缺陷,更多的是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后酿造的“苦果”。为了扭转这一不良现象,我国的教育界尤其是道德教育理论工作者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研究主题,从理念、内容、方法、途径、手段和评价等方面均作了积极的探索,为提升学校育人质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成绩有目共睹。然而,统揽这些研究,对规范、维系和引领育人活动深入发展的制度文化却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学校文化建设和德育工作的一大漏洞或瑕玷。之所以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育人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本身就是由各种制度架构起来的特殊的社会组织。离开了制度维系与支撑,学校便会陷入无序和混沌之中,育人作用自是无从谈起。鲁洁教授在《德育社会学》一书中也明确指出,由于教育自身就属于制度性的活动,因此,“作为教育一个组成部分的德育,自然也是制度性的活动”[1]。在学校制度性的道德教育活动中,制度文化是人们创设各种制度的价值指南,直接决定着制度设计的优劣及人们对制度文化的认同心理及实施效果。“制度文化是制度的灵魂”[2],是人们认同与接纳制度的认知阈限。缺失了制度文化建设,实质上等于斩断了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升华的纽带,势必造成断裂和紊乱的不良格局,形成一个巨大“裂谷”,严重地腐蚀着青少年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生成。
社会体制转轨、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密切和加深了学校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学校文化育人效应的发掘与彰显,不仅需要物质文化的奠基和支撑,而且需要精神文化的浸润和滋补,更需要制度文化的引领和保障。学校制度文化是维系学校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本保障。对制度文化的认识、理解和执行不到位,必然牵绊制度更新的步伐,学校的道德教育工作便难以有序进行,何谈与时俱进,学校育人目标的达成自是困难重重。
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不可或缺性日趋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学校文化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校自身的认肯与高度关注。学校文化是一个学校综合实力的表征,是学校的价值追求与灵魂所在,映射着学校的办学传统、办学优势和社会声誉。学校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实质是文化的较量。为了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各学校着手文化建设,不遗余力地打造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校文化风格。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制度文化的人文精神与道德价值日渐凸显。
中国的文化博大深邃,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道德文化传统,以倡德、崇德、尚德而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凝心聚力,蓄积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学校肩负着传承丰富多彩、光辉灿烂、广博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把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伦理道德质料发扬光大,学校通过制度的形式将其稳定下来,在血脉中传承,并引领和规范青少年学生的行为,促使他们胸怀善念,砥砺善行,在学校中过一种积极向上的、有意义的生活,是青少年学生道德成长的宝贵的教育资源。所有的这一切,均向我们昭明着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在塑造个体良好道德人格上,学校制度文化功不可没。循此思路,学校通过制度文化培养具有良好美德的学生,不仅能够落实“立德树人”道德目标,推进学校道德教育工作的有序开展,也可创新学校制度文化安排,为学校制度文化建设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互补效应显著,这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合作共赢的良方,何乐而不为!
然而,当飞速前进的历史车轮驶过20世纪的旅程之后,21世纪以降,这是一个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多元化共生乃至相互摩擦并激烈碰撞的时代,知识信息呈现出几何级井喷式增长状态,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变迁引发经济结构、政治民主和科技文化的深层变革,已是锐不可当的时代潮流,其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并呈现出明显的加速扩张、持续蔓延的态势,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其进展之速、威力之大、范畴之广、意义之深,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所难以比拟的。这种变化,使我们享受到了科学技术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的便利,为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飞速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加速了人类走向文明和幸福之路的发展进程。
二
但是,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我们倍感惊恐,因为科技的发展无法规避现代性的危机,尤其是无法帮助人们摆脱极端世俗的囚锁和精神世界的空虚。人们不得不承受被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称为“现代性”的代价。作为传统的对立物,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尤其是要打破传统并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体制和道德文化格局。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种制度化的秩序,因而应从制度的维度认识和把握现代性,即“对现代性作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3]。制度的基本作用是形成秩序。任何一种制度的出台,均直接或间接地指向秩序。现代性所标榜的工具理性以及抛离传统秩序所造成的断裂,以异常激烈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传统学校教育展开了攻击,并逐渐瓦解、蚕食、击破传统的道德体系和文化认同范式,将其撕裂与肢解为“文明的碎片”。碎片取代了完好,部分取代了整体,致使各种不和谐音符与日俱增,文化冲突与道德失序自是难免。
诚然,以科技为动力的现代性大大地激发了人的内在潜力与创造精神,但同时也导致了其任意妄为的偏执,在“理性”“自由”“解放”的幌子下诱发了人们无所顾忌、无畏无惧的偏激行径,遮蔽与荒芜了精神家园。现代社会被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称为“无家可归的社会”。面对现代性引发的冲突与失序,需要人类利用道德理智、人文精神予以唤醒与观照。倘若一味地听之任之或应对不力,则会腐蚀人的精神支柱与理性信念,刺激他们无限的贪欲和追名逐利的行为,助长技术至上、物质至上、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恣意横行,导致信仰虚无和道德迷失。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欢娱,“人就要暗自反省:‘我哪儿做错啦?’……‘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4]。聚焦于学校道德教育领域,现代性的“脱域”刺激了学生自我放纵、盲目攀比、空虚浮躁的心态,助长了他们的失信、违规、忘义、斗殴甚至犯罪等种种非道德行为和反道德行为,加剧了社会不良风气的蔓延,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滑坡。
现代性的发展使人异化为贫乏的怪物。“人类患下了‘分裂症’。在物质方面人类已达到造物主的水平,几乎已经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但是在精神和道德发育方面,在自我认识、自我把握等方面,却是如此的发育不良,水平低劣。有人说得好:当代的人有太多的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5]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性引发了人们丧失本体性安全感所导致的种种不适,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与学校重教书而轻育人的不良现状是难以割舍的。被誉为“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的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认为,现代学校教育越来越偏离了自身运行的轨道,被功利所俘获和主宰,遗失了存在的本体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为,个人接受学校教育不是为了修身养性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生计,为了能在求职择业、岗位竞聘、公开选拔等环节中脱颖而出,捞取更多的“资本”;一个阶级接受更高级别的学校教育,如攻读研究生学位、做博士后研究人员、做访问学者等不是为了促进本阶层人员教育水准的提升,而是处心积虑地谋求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良方,进而战胜其他阶层;一个国家高度重视学校教育,不是为了提升国民的综合素养,而是为了在教育领域中占有制高点,获得教育话语霸权,进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震慑力。如此,人们接受教育不再指向内在的自身完善,而是指向外在的工具目的。这意味着,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更多的和更高级别的教育,与他们谋求功名利禄的急迫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倘若教育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无关,与个人找一份体面的、待遇优厚的工作无关,与驾驭和支配其他人或阶层的权利无涉,与提高自身的名望和地位无干,那么接受教育的人就会是凤毛麟角了。“按照我们的社会科学,我们在所有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上都可以是聪明的,或者可以变得聪明起来,可是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就得退回到全然无知的地步。我们对于我们据以做出选择的最终原则、对于它们是否健全一无所知;我们最终的原则除却我们任意而盲目的喜好之外并无别的根据可言。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6]此种思想严重地冲击着学校的办学方向和育人标准,进而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休戚与共。这为肩负育人重任的学校教育提出新的甚或无以预料的巨大挑战,势必影响或左右学校制度文化在育人活动中的取舍及其有效运作,成为学校教育无可回避的严峻课题。
三
在实际的道德教育活动中,充斥现代性的学校教育用得失的精确性考量僭越了善恶的界限,自身日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与缺陷,尤其是在制度文化建设上的不当或漏洞,难以使制度文化中的育人标准植根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沃土中,落实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与社会公众对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期许相差甚远。不少学校在育人活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式制度文化育人的偏失、非正式制度文化育人的乏力、制度文化实施机构育人的疲软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育人的质量。审理与剖析当前我国学校管理的现状,不难发现,很多学校没有科学合理地制定或执行制度,将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人为地割裂开来,引发了“有制度无文化”“有知识无道德”“有文化无道德”的不良情形。这意味着,不少学校既不是从学校文化建设的角度做出制度安排,也不是从制度育人的角度出发制定制度,而是为了学校需要制度这个大前提而进行制度设计,执着于功利主义情结之中乐此不疲,导致学校制度文化建设走向了反面。
在现实中,一些学校的师生员工对学校文化建设没有明确的概念,也不愿了解、讨论或追问学校文化建设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一些学校不仅缺乏凝聚全体师生的共同认可或追求的育人目标,而且也没有依据本校的实际情况,有效凝练学校的办学特色或学校文化。我们对于没有明确的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目标深感担忧。这是因为,缺失了目标导向,行动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美国著名学者约翰·I.古得莱得(John I. Goodlad)在其专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对多所学校进行实地调研的过程中,不难发现,不少学校的教育目标和学校实际提供的实现教育目标的条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或不同。[7]在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学校进行制度文化建设只重结果,轻视过程;只重数量,轻视质量;只重约束,轻视内化。为了求得当前一时之效而将育人的持续性和连贯性抛到九霄云外,此种做法与学校制度文化希冀的育人的终极追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在物质和技术的压抑下,也在物欲的冲击下,变成只讲物欲,不求精神,只顾现实,不讲将来,只按技术合理性行为,不要批判性和创造性,不求对终极价值的追索和生存意义的反思。”[8]学校教育功能的扭曲、育人价值的遗失、功利主义的施虐,导致道德教育被科技理性和实用主义所宰割,使得学校教育不堪重负,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此种学校教育是残缺不全的教育,拔高了实用性而损害了人性的品质,其对个体、对国家、对世界的精神摧残与毒害无穷。一如吕型伟先生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残缺是心灵的残缺,循此思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难不是核云盖顶,而是在于心灵的残疾、精神的贫乏、道德的沉沦。由此,他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道德教育是21世纪学校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因此,革除学校制度文化建设中的诸多弊端,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组合和运用,充分发挥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功能,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社会有用之才,既是学校制度文化理论研究的重任,也是学校道德教育的现实吁求。
此外,学校制度文化的僵化和形式化运作,导致学校管理者或教师以指令甚或高压的范式控制学生的言行,使得不少青少年学生感到学校道德教育的无聊、空寂甚或无助。尽管学校制度文化明文规定要调动师生员工参与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奢谈民主、自由、能动的参与方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峰回路转或大相径庭,并没有按照既定的要求去切实贯彻落实,这体现出极大的虚伪性或欺骗性。[9]这种脱节现象的存在,便是“有令不行”“阳奉阴违”“巧言令色”的表征,势必落入文化育人的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沼泽中难以自拔。“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10]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浪费了学校有限的道德教育资源,而且会助长学校部门的不正之风,污染和吞噬师生的灵魂,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道德价值观的侵蚀和毒害,更是罄竹难书。
当前,学校制度文化运行和发展中暴露出的流弊已经成为桎梏学校育人工作的一大顽疾,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立德树人”的发展步伐。无论是从理论维度而言,还是从实践层面分析,学校制度文化的育人机制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尚处于起步阶段和摸索状态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学校制度文化育人功效的发挥,延缓或羁绊了育人的步伐,影响了学校道德教育体系的完善与成熟。为此,培育积极向上的学校制度文化,将学校制度文化与道德教育整合起来,深入探寻学校制度文化育人的原则和策略,发掘育人价值,探索育人规律,拓宽育人途径,使学校教育沿着完善人格的轨道稳步前行,开辟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视景,方可为学校制度文化建设注入新的血液和活力,稳定有序地提升道德教育质量或育人水准。
[1] 鲁洁:《德育社会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2] 车洪波、郑俊田:《中国当代制度文化建设》,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
[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9页。
[5] 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6]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7] John I. Goodlad,A Place Called School,New York:McGraw-Hill,1984,p.280.
[8] 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9] John I. Goodlad,A Place Called School,New York:McGraw-Hill,1984,p.241.
[10]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看哪这人:尼采自述》,张念东、凌素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