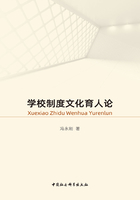
第四节 学校制度文化之于学生道德行为之养成
道德行为一直是研究者密切关注的议题。人的道德行为究竟由何而来?柯尔伯格从认知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休谟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情感是促使道德行为的催化剂;康德从意志的角度出发,认为善良意志是道德行为形成的关键。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道德行为产生的条件。但道德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可能是由某一个方面,或认知、或情绪、或信仰等引起,也可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更多的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道德行为是个体履行道德责任时道德意愿和道德动机的外部表现,是行为主体表现出的利他或利己的行为。
黑格尔高度评价道德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就是由其一整套道德行为构成的有机体。道德行为是衡量个体道德品质的重要尺度,其地位举足轻重。没有外在道德行为,人就无法和动物区别开来,就会陷入一种不可知论。尽管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评价学生的品德,但无论何种情况,道德行为均不能缺席,否则,不仅无法准确认识与判断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程度,而且助长了“口号式”道德教育的滋生与泛滥,其弊端不言而喻。“制度是人的行为方式,记录着这种行为所达及的领域和程度。”[30]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离不开学校制度文化的规范、保障和促进。在塑造学生良好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了学校制度文化在引领学生主动实践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性,通过建章立制、行为预期、规范运作、指引发展等活动推进学校道德教育工作,为学生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提供发展方向和行动指南。
一 促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道德行为方式
学生道德行为的产生与表现,要以掌握一定的道德行为方式为基本条件。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学生不愿意遵守道德,而是缺乏得当的行为方式,因而表现出一些不合理甚或并非有意为之的偏激行为。如把扰乱课堂秩序当作“勇敢”,把顶撞师长视为“英雄气概”,把帮别人打群架看作“讲义气”,等等。学校制度文化划定了学生自由行动的范围和界限,构成了引导或规范学生行为的指示系统。“制度是稳定地组合在一起的一套价值标准、规范、地位、角色和群体……它提供了一种固定的思想和行动范型,提出了解决反复出现的问题和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方法。”[31]聚焦于学校立德树人活动中,学校制度文化通过显性的制度条文,将学生的进退之节、处世之道、立身之本以明确的条款方式呈现出来,成为学生共同遵守和严格执行的行为规范,指引和规范着他们的言行举止,使学生的生活作息、日常学习、游学交友、考核评定等都有章可循,这对于学生基础文明行为的养成是大有益处的。
学校制度文化是对师生员工行为方式的刻画与描述,是对他们的交往行为和活动规则的整体性记录。有效地利用制度文化传递的信息,为学生感知、理解、巩固、运用道德规则提供了保障与预期,可规范学生行为,其在学生认识和掌握道德行为方式中的意义自是毋庸讳言。享有“现代教育之父”之称的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 Amos Comenius)特别重视行为规则或纪律在学生掌握正确道德行为中的作用,提出了许多促使学生实现动机的行为方式。他认为,倘若学校中没有规范学生行为的各种纪律,必将导致道德的无序或混乱。因此,“要经常地、高度警惕地维护准则。否则没有任何规章和有章不循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区别了”[32]。这在法国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道德教育》一书中也得到了体现。“社会生活不过是各种有组织的生活形式中的一种而已,所有现存的组织都以某些明确规范为前提,倘若忽视了这些规范,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混乱。”[33]尤其是在由各种规章制度组成的学校这个教育组织,促使学生明确并遵守规范,便成为有序行为的基本保障。
学生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生成,具有长期、反复、波动的特征,必须经过持久的、一贯的、常态化的培养,方得以有效养成。契合学生年龄特征的学校制度文化,具有规范行为与纠偏的功能,特别是在引导学生获得正确行为方式和提升学生的道德意识等方面效果显著。一方面,教师通过对制度规则的讲解,使学生明确了最基本的规则与行为要求,逐渐放弃原有的非道德动机,习得正确的道德行为方式。加之教师以身示范,模范遵守制度规则,学生心领神会,师生心有灵犀,强化了学生对制度规章或道德准则的认可、理解和接纳,并作为支配自己行动的指南,加之通过反复练习和不断实践,形成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稳步趋达道德教育的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常态化的行为管理制度,制度文化的规范化运作,尤其是班级管理制度细则、考试违规处理条例、课堂纪律管理制度以及主题班会制度的切实贯彻落实,引导学生按规定的方式一律行动,对学生的一些违规行为予以纠正,有助于深化学生对偏离道德行为的认识与判断,减少个人行动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在认同道德规则的基础上尊崇道德,向往道德,转化为自己内在的认知需求与行为动力,使之按照制度文化的要求表现出相应的道德行为,并不断得以巩固。
二 推动学生从知善到行善的转变
认知是行为的向导。但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二者经常会表现出不一致。知善既可以助推善的行为,也可以保持中立的旁观态度,还可反其道而行之,做出背离善的行为。“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贵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个人的无知而做错了事,并非本人的意愿,只有在引起他们的痛楚、内疚或悔恨时才有所醒悟。“一个人的无知,在于对自己是什么人,在做什么,在对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做什么的无知;有时候,也包括对要用什么手段——例如以某种工具——做,为什么目的——如某个人的安全——而做,以及以什么方式——如温和的还是激烈的——去做等等的无知。”[34]对于无知的行为,我们不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对处于“无律”阶段的儿童而言,他们表现出无知或不良行为,甚或一些偏激行为,我们不必过分指责他们,因为这是每个个体道德发展的必经阶段,学生正是在不断尝试错误、改正缺点以及习得正确的行为方式中不断成长和发展的。由于“无律”阶段的儿童尚不具备自主的道德判断,也不能充分意识到错误行为的危害性,因而我们必须加强引导,丰富儿童有关的道德概念,激发儿童与道德情感相一致的行为,促进儿童的道德体验不断深化。但人的道德认识能力和概括水平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能以无知而推脱个体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当个体的道德发展进入“已知”状态时,即将道德规范或善恶标准背得滚瓜烂熟,却不去支配自己的行为,就不能不引起教育工作者的警惕和担忧。聚焦现实,体察当下,一些学生不是出于道德上的无知,而是实践过程中的不为。“有所谓的‘是非’观念或道德知识,对真实生活中的道德是非却无动于衷(感情上的麻木和冷漠);明明知道某种行为是错误的,但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去做了;知道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很多道德知识,但根本不能或不愿意去实践道德行为。”[35]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严重错位,或知善不为,或阴奉阳违,这是对道德的公然挑衅,吞噬着学生的精神信仰,导致德性大厦的倒塌。“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理解行为所应遵循的准则,这是‘知’的方面;更必须在生活上遵循这准则而行动,这是‘行’的方面;必须具备两个方面,才可称为有道德的人。”[36]因此,通过学校制度文化建设矫正不良行为,实现知善到行善的转化,养成知行合一的良好品质便被提上日程。
学校制度文化以促进学生道德成长并丰盈人性为价值追求,其“任务是培养真正的人性。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尊重的崇高道德的和人道的行为,是社会道德进步的条件和形成人的高尚品格的保证”[37]。学生之所以知行断裂,明知故犯,做出本应完全可以避免发生的不道德行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和规章制度约束的缺席。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以及实用主义的抬头,导致部分学生理想信念动摇,道德行为迷失。倘若制度文化坐以待毙,不能对学生的不当行为作出规约,而讲求实用性的投机者又不能以极强的耐心与克制力严格约束自己,致使他们的不道德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其危害性是不可小觑的,不仅为信奉“对我有用就是善”的享乐主义者打开方便之门,而且极易产生暗示或趋同效应的不正之风,诱发其他学生的仿效心理,助长了道德行为的失范。制度文化运行过程中惩戒作用的发挥,使得学生为不道德行为付出了严重代价,如中小学生考试作弊不仅取消该门课程的成绩,而且全校通报批评,甚或装其档案袋等,对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依据其情节的轻重给予取消先优评选、留校察看、吊销学位等。惩戒的运用,可能会引发学生意志消沉、空虚烦躁和自暴自弃的心理,但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逐渐意识到自我约束在确立道德纪律并形成合乎道德的行动中的重要性,深刻体验背道离德的羞耻感或自责感,逐步纠正不良行为,将外部的制度约束如遵守秩序、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等内化为良好的品德与行为习惯,实现道德的内化,积极行善,形成表里如一的文明习性和基础道德素养。“只有在自我控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确立道德的纪律。它告诉我们,不要出于转瞬即逝的冲动来行动,也不要不论愿意与否,把我们的行为置于自然倾向的水平上。它告诉我们,行为中有一种努力;只有当我们限制某些倾向,压制某些欲望,减弱某种趋势的时候,行为才能成为合乎道德的行动。”[38]
三 引导学生自觉自愿地践履道德行为
学生的道德自觉性是衡量学校立德树人效果的重要尺度。培养学生的道德自觉性尤其是道德自律行为便成为有效道德教育的重要表征。从掌握道德行为方式到知行合一,再到主动行善,是学校制度文化指引学生行为并推动他们良好道德品质养成的三个环环紧扣的步骤。以学校制度文化建设为着眼点,就是要使学生意识到道德责任的重要性,萌发持久而强烈的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调节行为。“全部道德文化的主要目的是塑造和培养理性意志使之成为全部行为的调节原则。”[39]在引导学生遵守日常行为准则和调节学生行为的基础上,不断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与自觉精神,使道德行为成为他们的内在自觉。长此以往,道德知识的传承,道德情感的激发,道德行为的彰显,定然会在学校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学校要培养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一定是自觉追求道德行为的人,其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必须是持久的、稳定的、连续的、一贯的。在这里我们要避免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将个别的行为、偶然的合乎道德标准的行为视为衡量个体道德的标准;二是将一个人在一个领域持续的道德举止视为个体是有道德的。一个具有真正道德的人,应该是在任一领域或任意活动的任一时期表现出一系列行为的综合。如果一个学生在校期间一直是遵守道德、文明礼貌的好学生,但在家里却飞扬跋扈、随心所愿、任意妄为,这在两个领域“两张皮”现象的存在,就不能说学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学校制度文化通过明理导行的方式,规约与道德要求和普遍意志相背离的行为,发展学生互惠、合作的行为,引导学生找准人生的发展方向,让道德行为成为学生的自主选择。一如美国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言,道德行为必须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这个行为的前提是当事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做什么背后包含的道德意义。学校制度文化从规约学生行为到引导他们的自觉自为,是一个让学生接受道德训练的过程,是唤醒学生道德良知的过程,使之懂得合作,诚实守信,拥抱美德。
学生依据制度文化对道德行为的预期,体验遵守制度规则获得成功的愉悦感与自尊感,表现出积极向上的驱动力,通过制度激励而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效地发挥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深刻认识道德责任和人格尊严,在自我约束、自我肯定与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真正认可与接纳制度文化中的道德规则,保持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接受深刻的精神洗礼与品格砥砺,感受到道德的美好与尊贵,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人是道德行为的真正执行者,道德作用机制的现实启动者,而且只有人才能在自己对象性活动中不断完善社会关系,在接受社会规范制约的同时,能动地改造规范并完成对自己的肯定,表现出人的自为性特征。”[40]在制度文化启动学生自觉道德行为机制的作用下,学校便会成为学生道德成长与发展的舞台,道德生命在这里得以张扬,人文精神在这里得以彰显,人生价值在这里得以逐步实现。
[1] 杜时忠:《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年第1期。
[2] [美]R.A.巴伦、D.伯恩:《社会心理学》,黄敏儿、王飞雪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3]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教育论著选》,卢濬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4]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9页。
[5]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教育论著选》,卢濬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75页。
[7]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1页。
[8] 曾小华:《文化·制度与社会变革》,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10] 冯永刚:《刍议制度文化在道德教育中的功效》,《教育研究》2012年第3期。
[11] 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12] [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页。
[13] [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14] 周辅成:《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5页。
[15]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51—652页。
[16]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7] [美]马丁·L.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杨韶刚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8] [英]弗·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页。
[19] 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20]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页。
[21] 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22] 许和隆:《冲突与互动:转型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制度与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23] [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行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4] [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行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代序,第3—4页。
[25] 杨祖陶、邓晓芒:《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26] 冯契:《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5页。
[27]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8页。
[2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5页。
[29] [美]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何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30] 王海传:《人的发展的制度安排》,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31] [美]伊恩·罗伯逊:《社会学》,黄育馥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9页。
[32] [捷]夸美纽斯:《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选编,任宝祥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33] [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3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2—63页。
[35] 魏贤超:《德育课程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
[36]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7] [苏]瓦·亚·苏霍姆林斯基:《学生的精神世界》,吴春荫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38] [法]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39] [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
[40] 戚万学:《活动道德教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