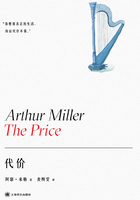
第4章 第一幕1
今天。纽约。
舞台后方是两扇窗。日光透过灰蒙蒙的格子窗照进来,窗户上有白色涂料打的叉,这幢楼面临拆除。
此刻,日光从屋顶的天窗透进来,因为肮脏的玻璃而显得灰暗。顶上透进来的光先打在舞台中央一把又厚又软的扶手椅上,椅子上罩着褪色的玫瑰红椅套。扶手椅右边是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台二十年代的金属丝花面收音机和旧报纸;扶手椅后面有一盏落地灯;左边是一台装有发条的老式留声机,还有一张矮桌,上面放着一叠唱片。不远处有一块白色抹布、一个拖把和一只水桶。
房间是逐渐显露的。只有扶手椅周围这块区域,连带另几把椅子和一张沙发,看上去像被占用过。这块区域以外,到房间两侧、顶后面、贴着墙从地板到屋顶,一片混乱,仿佛十个房间的家具都被硬塞入这一个房间内。
地板上横七竖八地放着四张沙发和三把长沙发椅,另有扶手椅、单人高背沙发、一张卧榻和其他几把散放的椅子。靠着三面墙直堆到天花板上的有梳妆台、大衣柜、一张高高的秘书桌、一个中凸橱柜、一个有精美雕花的长送餐桌、几张茶几、一张大书桌、好几张办公桌、几个玻璃门书橱、弓面玻璃陈列柜等等。几张地毯卷在一边,有长有短。还有一支长桨,若干床架、大箱子。一大一小两盏水晶灯吊在绳子上,没接电线。十二把餐椅沿左侧一张餐桌一字排开。
这些家具给人一种强烈的厚重感,几乎有些德式特色。依墙而立的橱柜凸起的橱面、弯曲的线条承载了时间的重量。整个房间拥挤得可怕,难以插足,简直让人难以判断这些东西是壮观还是仅仅过于厚重、丑陋。
一架竖琴,没罩上罩子,镀金都已剥落,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方右侧。后方,凑合着挂上一张帘子,早已褪色,帘子后面能看见一个小水槽,一台电炉及一个旧冰柜。右边靠前有扇门,通往卧室。左边靠后,另一扇门通往看不见的走廊和楼梯。
我们置身于曼哈顿一幢即将被拆除的褐砂石住宅楼的阁楼上。
身穿制服的警官维克托·弗朗茨自左侧门进,在屋里停下,环顾四周,随便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下。他面无表情,却不知怎的被屋子释放的某种气场镇住了,目光一点一点移动着,一件一件地打量着家具,将整个房间难以言喻的景象尽收眼底。
他朝那架竖琴走过去,神情颇为严肃,仿佛走近的是一具棺材。他在琴前停下,伸手拨了一根弦。他转过身,走向餐桌,解下带枪套的腰带,脱掉外套,从桌上倒扣着的三把椅子中拿下一把,将腰带、外套挂在上面。
他看看表,等待时间过去。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留声机前的那一叠唱片上。他掀开留声机盖,看见唱盘上已有一张唱片,他转动手柄,把唱臂移到唱片上放好。加拉格尔和谢恩[19]的歌声响起,他听着那老掉牙的歌声微笑起来。
唱片就那么响着,他走向倚在家具上的那支长桨,摸了摸。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够到一个柜子后面,拽出一把花剑和面罩。他在空中把剑甩得噼啪作响,目光被回忆占据。他把剑和面罩放在桌上,在那叠唱片里翻了两三张,看到某张唱片上的标题时禁不住满面笑容。他把留声机里的加拉格尔和谢恩取出,换上这张。这是一张《笑声集锦》——里面两个男的笑得歇斯底里,再怎么尝试都没办法说出个完整句子。
他笑着,笑容在脸上扩大,笑出了声,然后开怀大笑。他被戳中笑点,笑得更厉害了。这会儿他笑弯了腰,抑制不住踉跄了一步。
他的妻子埃丝特自左侧门进。他背对着她。她四下张望,想看看是谁在跟他一起笑,自己脸上也露出笑意。她朝他走过去,他听见她高跟鞋的响声,转过身。
埃丝特 那到底是什么啊?
维克托 (吃惊地)嗨!(他抬起留声机的唱臂,脸上还笑着,有点不好意思)
埃丝特 听起来像个热闹的聚会!
[他在她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指向唱片)那是什么啊?
维克托 (试着掩饰他的不满)你去哪儿喝的酒?
埃丝特 我告诉过你的,我去体检了。(她笑起来,一副明知故犯的表情)
维克托 好家伙,你和那个医生。我以为他告诉你不要喝酒。
埃丝特 (笑)我就喝了一杯!一杯不会对我有什么坏处。反正一切正常。他向你问好。(她环顾四周)
维克托 是吗,那太好了。交易商马上就来,你看要不要拿点什么。
埃丝特 (环顾四周,叹了口气)噢,我的天——又回到这儿来了。
维克托 那老太太干得不错。
埃丝特 是啊——我还从没见过这屋里这么干净。(指着房间)你觉得滑稽吧?
维克托 (耸肩)没有,没怎么觉得——她都没认出我,你能想象吗?
埃丝特 我的天,一百五十年呐。(一边四处张望一边摇头)呵。
维克托 你说什么?
埃丝特 我说时间。
维克托 是的。
埃丝特 这间屋子有点儿不一样了。
维克托 没有,完全是以前的样子。(指着房间一边)我的书桌和小床一直摆在那边。屋里其他都没变。
埃丝特 也许是因为以前它对我来说显得过于讲排场,有点庸俗。不过,它也确实有种个性。想不到有些东西现在又时兴了。
维克托 嗯,有什么是你想要的吗?
埃丝特 (环顾四周,犹豫不决)我不知道我想不想把这些东西放在身边。它们都这么大……放哪儿好呢?那个柜子挺好看的。(她朝柜子走过去)
维克托 那是我的。(指向对面的另一个柜子)那边那个是沃尔特的。它们是一对。
埃丝特 (比较着)哦,是啊!你联系上他没有?
维克托 (移开目光,仿佛遇到一个难题)今天早上又打过电话——他在会诊。
埃丝特 他在办公室吗?
维克托 在。护士过去跟他说了声儿——无所谓。只要通知到他,我这边就可以继续。
[她克制住,不予置评,拿起一盏台灯。
那可能是真的陶瓷。放在卧室也许不错。
埃丝特 (放下台灯)要么我们约好在哪儿见吧?这整件事让我感到沮丧。
维克托 为什么?不会很久的。放松些。来,坐下吧,交易商随时会到。
埃丝特 (坐在沙发上)这地方给人一种腐烂变质的感觉。我就是忍不住会有这种感觉,一直都有。这儿的一切都叫人窝火。
维克托 好了,别激动。我们会把它卖掉,然后一切到此为止。对了,我买好了票。
埃丝特 哦,那好啊。(头向后靠去)啊,但愿是场好电影。
维克托 最好是。不单单好,要特别棒才行。两块五一张呢。
埃丝特 (突然不服气地)我可不管!我就是想出去走走。(她不再进一步回应,而是环顾四周)天哪,这都是在干什么啊?刚才上楼的时候,看到所有门都敞开着……看起来不像是……
维克托 这一周他们每天都在拆除这些老旧的建筑,宝贝。
埃丝特 我知道,可是这让人感觉像活了一百岁一样。我讨厌空房间。(陷入沉思)那个古怪的家伙叫什么来着?就是租了前厅的那个,记得吗?——修萨克斯管的?
维克托 (微笑着)哦——萨尔茨曼。(伸出手朝一侧比划着)一只眼朝那边斜。
埃丝特 对!我每次下楼,他就虎视眈眈地等在那儿!他是怎么搞到那么多漂亮女孩的?
维克托 (笑)天知道。他身上的气味儿一定不错。
[她笑起来,他也笑。
其实有时候他还会跑上来,半下午的时候,说:“维克托,快下来,我有多余的!”
埃丝特 然后你就真下去了!
维克托 干吗不去啊?如果是白送的,你就欣然接受。
埃丝特 (脸红起来)你以前都没告诉过我。
维克托 没有,那都是在遇到你之前。大部分是。
埃丝特 你真下贱。
维克托 那又怎样?那是大萧条时期。
[她对这不合逻辑的回答哂然一笑。
不是,说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友善,更多是在大白天乱搞。像麦克洛克林姐妹——记得吗,在前面的卧室给人提供打字服务的?(笑)我父亲总说:“这样的打字服务,打一张得两块钱。”
[她笑。笑声逐渐平息。
埃丝特 这些人可能都死了。
维克托 估计萨尔茨曼是死了——他身体一直不错,不过——(他摇了摇头,吃惊地轻轻一笑)唉,也不是。我想他那时候差不多……是我现在这个岁数。呵!
[他们突然意识到了时间的威力,在沉默中怔了片刻。
埃丝特 (起身,朝那架竖琴走去)好吧,你的交易商人呢?
维克托 (瞥一眼手表)现在五点四十。他应该很快就到。
[她拨起琴弦。
这东西应该值些钱。
埃丝特 我想这儿的很多东西都挺值钱的。但是你得讨价还价,你知道的。不能他们说什么价你就卖什么价。
维克托 (略带抗议)我会讨价还价;别担心,我不会白送人的。
埃丝特 因为他们是准备好要讨价还价的。
维克托 别这就泄了气,行吗?我们甚至都还没开始呢。我是打算讲价的,我可知道那些家伙的真面目。
埃丝特 (不再继续争论,朝留声机走去,试图营造出欢乐的氛围)这是什么唱片?
维克托 《笑声集锦》,二十年代很红的。
埃丝特 (好奇地)你还记得这个?
维克托 模模糊糊记得。我那时才五六岁。聚会上常放这种唱片。你知道的,就是看谁能忍住不笑。也可能大家只是为了坐在一起笑,我也不大清楚。
埃丝特 这想法真不错!
[可以说这会儿他们之间的交流趋于缓和;他转向她。
维克托 你看起来不错。
[她看着他,尴尬地笑了下。
我是说真的。都说了会讲价,为什么你……
埃丝特 我相信你。这就是我买的那身儿。
维克托 啊,就是这件啊!花了多少钱买的?转过去看看。
埃丝特 (转起来)四十五,想不到吧。他说没人愿意买,嫌它的样式太简单了。
维克托 (领会到了两人之间的共识)好家伙,那些女人真是笨,这件多漂亮啊。瞧,如果花钱能买到像样的东西,我是不会介意的,不过他们卖的东西一半都是垃圾……(向她走过去)对了,看看这衣领,这不就是你最近买的其中一件吗?
埃丝特 (检查一番)不是,这件是以前买的。
维克托 好吧,即便如此(抬起一只脚后跟),应该给消费者联盟写信投诉这双鞋的鞋跟。才穿了三个星期——你看看!
埃丝特 是你走路姿势不正。你不会要穿着这身制服跟我出去吧。
维克托 真该杀了那家伙!我刚换上便服,麦高恩正试图采集某个流浪汉的指纹。对方不想按指纹,所以就甩开胳膊,我正好经过,他就把我的杯子打翻了。
埃丝特 (知道这大概意味着什么)哦,我的天……
维克托 脏衣服已经送去干洗店了,他们会尽快处理,六点前洗好的。
埃丝特 你那咖啡里加了奶精和糖吗?
维克托 加了。
埃丝特 那六点前绝对洗不好。
维克托 (安抚她)他们会尽快的。
埃丝特 哦,算了吧。
[稍作停顿。她失落极了,心不在焉地四处张望。
维克托 好了,不过是看场电影……
埃丝特 但是我们难得出去——为什么所有人都得知道你挣了多少钱?我想安安生生地过一晚上,安安生生地在餐馆里吃顿饭,不要有什么喝醉了的、以前做过警察的家伙过来跟你谈什么过去的事。
维克托 这事就发生过两次。这么多年了,埃丝特,在我看来……
埃丝特 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就拿在博物馆碰上的那个人来说吧,他真的以为你就是那个雕刻家。
维克托 那我就是个雕刻家咯。
埃丝特 (愠怒)可以,很好,就这样吧!你真的,维克——你穿那套正装当真显得气度不凡。所以干吗不穿呢?(头靠在沙发背上)我真该记下那瓶苏格兰威士忌的名字。
维克托 所有苏格兰威士忌的化学成分都一样。
埃丝特 我知道;不过,有些味道更好。
维克托 (看手表)你看看,这像话吗?说好的五点半整。个个儿都信口开河。(他来回走动,越来越焦躁,尽量压抑自己因她的情绪而起的怒气。他的目光落在一个五斗橱半开的抽屉上,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只冰鞋)看这个,还是好好的!(他用手指甲试了试冰刀;她仅仅瞟了他一眼)甚至还很锋利。我们什么时候该去滑冰。(他意识到她的情绪毫无起色)埃丝特,我说了我会讲价的!——知道了吗?——你根本不懂怎么喝酒;酒只会让你郁闷。
埃丝特 是吗,可这种郁闷我喜欢!
维克托 老天爷。
埃丝特 我有个主意。
维克托 什么?
埃丝特 干吗不叫我自己待着?给我点喝酒抽烟的钱就行。
维克托 那你就永远不用从床上爬起来了。
埃丝特 我会起来的,偶尔。
维克托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你干吗不去和你的医生待几个星期?我是认真的。也许你会有所改观。
埃丝特 要真能那样就好了。
维克托 好啊,那你去啊。他也有正装。你甚至可以带着那条狗——尤其是那条狗。(她笑)这没什么好笑的。每次你出去雨中散步的时候,我都很紧张,不知道你会带回来什么。
埃丝特 (笑着)哦,接着说,你爱她。
维克托 我爱她!你喝醉了酒,你往家里带莫名其妙的小动物,又说我“爱”它们!我才不爱那条该死的狗!
[她深情地笑起来,也带着某种女性特有的挑衅。
埃丝特 好啊,是我想要她!
维克托 (停顿)一条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埃丝特。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女人,不能终日无所事事。哪怕找份兼职工作,也能让你有个地方去。
埃丝特 我不需要去什么地方。(稍作停顿)我还不太习惯理查德不在家的日子,仅此而已。
维克托 他走了,宝贝。他长大成人了,你得自己做点什么。
埃丝特 我不能日复一日去同一个地方,以前不能,以后也绝无可能。你要求跟你哥说话了吗?
维克托 我问了那个护士。是的,我要求了。他走不开。
埃丝特 那个狗娘养的。恶心。
维克托 可是你又能拿他怎样呢?他从来没有那种感觉。
埃丝特 什么感觉?十六年过去了才来接一次电话?这是基本礼节。(忽然流露出那种至亲间的同情)你怒不可遏,是不是?
维克托 我只是气我自己。我这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地给他打电话,像个傻子似的……让他见鬼去吧,我自己处理,这样正好。
埃丝特 他的那份怎么办?
[他动了动,感觉受到了逼问,有些气恼。
我不想惹你讨厌——不过,我想,这里有钱的问题,维克。
[他沉默不语。
你会跟他提钱的事,对吗?
维克托 (一副心意已定的样子)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有权得到他那一半,他为什么要放弃?
埃丝特 我以为你决定直接跟他摊牌。
维克托 我改变主意了。我不觉得他欠我什么,我不能假装他欠我的。
埃丝特 可他有多少辆凯迪拉克呀?
维克托 这正是他有那么多凯迪拉克的原因。爱财之人是不会把钱拱手送人的。
埃丝特 我不懂你为什么总把这说得像做慈善。有一种东西叫道德债务。维克,你成全了他的全部事业。什么法律规定只有他能学医——
维克托 埃丝特,拜托——我们别再旧事重提了,好吗?
埃丝特 我没有旧事重提——你甚至比他学习还好。那确实是他欠你的债,该有人叫他去面对。如果没你照顾老爸的话,他不可能读完医学院。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该开始像正常人那样去谈论这件事!这里头可能有一大笔钱。
维克托 我觉得不太可能。这里没有古董,也没——
埃丝特 难道就因为是我们的东西,就一定不值钱吗?
维克托 这又是什么话?
埃丝特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一点不假!
维克托 (疾言厉色)那人甚至都不接电话,我能怎么——
埃丝特 那你就去给他写封信,去敲他的门。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维克托 (大吃一惊,意识到她的郑重其事)你为什么这么激动?
埃丝特 这么说吧,一个原因是,这也许能帮你下决心从岗位上退下来。
[稍作停顿。
维克托 (小心翼翼地、不情愿地)不是钱的问题。
埃丝特 那是什么的问题?
[他沉默不语。
我只是觉得有了这笔卖家具的钱作缓冲,你可以考虑一两个月,看看能想到什么事情是你愿意去做的。
维克托 这就是我现在考虑的全部问题,不是只有辞了职才能去考虑。
埃丝特 但是你好像没考虑出来什么。
维克托 这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快五十了,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开始一份新的事业。我不懂为什么这事突然就变得迫在眉睫了。
埃丝特 (笑)突然!自从你符合退休条件以来,我就一直在说这事——同一件事我已经说了三年了!
维克托 好了,这还不到三年——
埃丝特 到三月份就三年了!是三年。如果你那时候就回学校的话,现在硕士学位差不多也到手了;你也许已经有机会开始做你喜欢做的事了。不是吗?你为什么就不能有所行动?
维克托 (停顿,几乎有些无地自容)跟你说实话。我感觉这一切都不太真实,等我能开始做点什么的时候,我都得五十三、五十四了。
埃丝特 可你是一直知道这点的呀。
维克托 真正事到临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不确定这么做还有没有意义。
埃丝特 (走到一边去,声音中含着绝望)好吧……这正是我以前无数次试图告诉你的,这么做以前有什么意义,现在就还有什么意义。你可能还有二十年,其实这仍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很多有意思的事。(稍作停顿)你还这么年轻,维克。
维克托 我还年轻?
埃丝特 当然!我不年轻了,但是你还行。天,所有女孩子都爱盯着你看,你还想怎么样?
维克托 (空洞地笑)埃丝,这很难说,因为我不明白。
埃丝特 那为什么不谈谈你到底不明白什么?为什么指望你自己是什么都懂的权威?
维克托 可是,我们总得有个人挣钱,宝贝。
埃丝特 你是想让我假装一切都好极了?我已经不知如何是好了,我不会假装太平无事!(仿佛压抑许久似的一吐为快)我说叫你写信给沃尔特,说了有五十遍——
维克托 (好像听到一个重复多遍的故事)怎么又和沃尔特有关?沃尔特能做什么——
埃丝特 他是个有名的科学家,他那个医院在建一个全新的研究部门。我在报上看到了,是他的医院。
维克托 埃丝特,那人十六年来没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埃丝特 可是你也没给他打过!
[他吃惊地看着她。
嗯,你没打过。那也是事实。
维克托 (她的话似乎令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确实也没给沃尔特打过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干什么?
埃丝特 因为他是你哥哥,他有权有势,他可以帮你——对,人们都是那样做的,维克!他写的那些文章透露出真正的理想主义,有实实在在的人性关怀。我是说,人是会变的,你知道。
维克托 (转过身)抱歉,我不需要沃尔特。
埃丝特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认同他;他是个自私的混蛋,但他或许能帮你走上正轨。我觉得这没什么丢脸的。
维克托 (感觉受到逼迫,怒不可遏)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突然变得这么紧急。
埃丝特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境地,维克托!(她说到最后几乎尖叫起来,自己也吃了一惊。他沉默了。她平静下来)要是我知道行动背后的原因,我会为此付诸行动,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说,一旦拿到养老金,我们就能开始真正的生活了……这就好像二十五年来一直在推一扇门,现在门忽然开了……而我们就站在那儿。有时我想,也许我误解你了,也许你挺喜欢警局的工作的。
维克托 我无时无刻不在恨它。
埃丝特 我全做错了!我发誓,我觉得如果我过去要求更多的话,本可以更好地帮到你。
维克托 不是那么回事。你一直是个很棒的妻子——
埃丝特 我想我不是。但安全感对你来说那么重要,以至于我总试图顺着你;可是我错了。老天——来这儿之前,我在家里看了一圈,想看看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拿回家用的——家里的一切都不堪入目,破旧、寒碜、俗不可耐。而我是有品位的人!我知道我是!只是对我们来说一切总是暂时的,好像我们从来就什么也不是,总是将要成为什么。我回过头去想打仗的那段时间,随便什么蠢货都赚得盆满钵满——那时候你就该辞职的,我就知道该这样,我就知道!
维克托 那时候我是想辞职的。
埃丝特 我只喝了一杯,维克托,所以,别——
维克托 别改变整个故事,宝贝。我是想辞职的,可你害怕了。
埃丝特 因为你说战后会有大萧条。
维克托 好吧,去图书馆查一九四五年前后的报纸,看上面是怎么说的!
埃丝特 我才不在乎!(她转身——回避自己的蛮不讲理)
维克托 我发誓,埃丝,有时候你说得好像我们从未有过自己的人生。
埃丝特 老天——我妈说得真对!我总是不信眼见为实。我早就知道如果你战时不辞职,那你就永远也不会辞职——我任这一切发生,什么也没说。你知道我们该死的麻烦是什么吗?
维克托 (瞥了一眼手表,感觉到她的抗议已接近尾声)是什么?
埃丝特 我们从来也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钱上!我们为它发愁,我们把它挂在嘴边,但我们好像不能想要它。我想要,可你不想。我真的想要,维克。我想要它。维克,我想要!
维克托 恭喜你。
埃丝特 去死吧你!
维克托 我希望你能别再拿自己跟其他人比了,埃丝特!你最近一门心思扑在这上面。
埃丝特 可我控制不了自己!
维克托 那样的话你必输无疑,宝贝,因为你的前面总会有别人。这是怎么了?我生性不好跟人攀比,你也有你的性情——我没变——
埃丝特 可是你变了。自从退休的事提上日程,你就变得像行尸走肉一般,浑浑噩噩——
维克托 可这到底是个要做出的决定。我希望能更有把握……其实有那么几次我都已经开始填表了。
埃丝特 (警觉地)然后呢?
维克托 (吃力地——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这种难以启齿)我想这里面有某种终结的感觉……(他突然说不下去)
埃丝特 但除此之外你还指望什么呢?
维克托 这很蠢,我承认。但当你看着那该死的表格时你会情不自禁。你给这二十八年签上名,你禁不住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全部?就这样?当然就这样。问题是,当我考虑新的开始时,那个数字就跳出来——五十,天啊——我就泄了气。不过,我一定会做些什么的。我会的!(努力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次一想到这一切——都有点不寒而栗。
埃丝特 你指什么?
维克托 就好像我之前到这儿时……(环顾四周)整件事——都让我感到某种疯狂。把所有东西堆在这儿,好像它们都是金子做的,(似笑非笑,露出近乎尴尬的神情)家具一件不剩地都搬上来,差点连地毯钉条都保留下来。(转向舞台中央的椅子)从始至终我都陪着他——现在于我而言简直无法想象。
埃丝特 (同情中流露出更多的遗憾)唉……你是爱他的。
维克托 我知道,但那就是说说而已。他是什么?一个破产的生意人,和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我那时感觉像天塌了下来。跟你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整件事就像别人给我讲的故事一样。你有过那种感觉吗?
埃丝特 嗯,每一天,无时无刻。
维克托 哦,得了吧——
埃丝特 是真的。我第一次踏上这里的楼梯时才十九岁。还有你打开那个装着你第一套制服的盒子时——记得吗?你第一次穿上制服的时候?——我们笑成什么样?你说如果有事的话你要叫警察!(他们都笑起来)跟化装舞会一样。我们是对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对的。
维克托 (因她的痛苦而痛苦)你知道,埃丝特,你时不时就想闹回小孩子脾气,那——
埃丝特 我就是想!我厌倦了——算了,别提了,我想喝一杯。(她去取手提包)
维克托 (吃惊地)你这是做什么?大冒险吗?你这么突然要去哪里?
埃丝特 我受不了这儿,我得出去走走。
维克托 你现在可别胡来!
埃丝特 我不是酒鬼!
维克托 你的生活和好多人相比都算是不错的!你是想变成讨人厌的十几岁孩子还是怎样?
埃丝特 (指着家具)别跟我说什么小孩子脾气,维克托——别在这间屋子里说!你任由这些东西堆在这儿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你连跟你哥简单谈一次都办不到,还说我使性儿?在那人面前你还是个十八岁的孩子!我的意思是说,对,我陷入了困境,可我敢于承认!
维克托 (被刺痛)很好,你继续。
埃丝特 (不能就这么离开)你有收据吗?我去给你拿你的正装。(他一动不动。她试图讲道理)我只是想离开这里。
维克托 (取出一张收据递给她。声音冷冰冰的)就在第七街,上面有地址。(他从她身边走开)
埃丝特 我马上就回来。
维克托 (任由她这样不负责任)随你的便,宝贝。我说真的。
埃丝特 你昨晚又磨牙了。你知道吗?
维克托 哦!难怪我耳朵疼。
埃丝特 真希望我有台录音机。我说真的,那声音让人毛骨悚然,听起来像很多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要是你能听见就好了,那你就不会这么不以为意。
[他沉默不语,一脸担忧,难过不已。他走向舞台后部,仿佛在查看家具。
维克托 没事。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埃丝特 (担忧地——试图微笑,转身朝他走过去)比方说?
维克托 (拉开一把椅子,膝盖微曲,拖出一台巨大的老式无线电底盘)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
[稍作停顿。
埃丝特 (试图缓和二人的关系)那是什么?
维克托 哦,我做的那些老无线电,这是其中一台。天啊,看这些管子。
埃丝特 (面对无线电有些感慨,但更多是好奇)还能用吗?
维克托 不能用了,需要一个蓄电池……(陷入回忆,突然抬头看向天花板)
埃丝特 (抬头看)上面有什么?
维克托 当时有节蓄电池爆炸了,正好冲到那上面某处。(指向天花板)那儿,看到那里的涂料不一样了吗?
埃丝特 (争取在二人之间制造火花)是你用它连上了东京信号的那台无线电吗?
维克托 (并未回心转意,声音毫无起伏)对,就是那大家伙。
埃丝特 (语气温和)干吗不留着它呢?
维克托 啊,留着一点儿用也没有。
埃丝特 你不是说过这楼上有个实验室吗?还是说是我在做梦?
维克托 是有,不过爸和我搬上来住时,我就把它拆了。以前那面墙归沃尔特所有,这面墙归我。我们在这里搞过一些很不错的发明。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避开她的目光,自顾自地走动着)坦白说,宝贝,当我回过头看那些过来的日子时,我只感到费解,我知道所有原因一切原因全部原因,可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他走到竖琴边,摸摸它)感觉很奇怪,知道吗?我全都忘记了——以前,我们有时候在这儿整夜忙活,房间里经常有音乐声响起。母亲会在楼下书房弹竖琴,一弹就是好几个小时,简直不可思议,因为竖琴的声音是如此轻柔,但我猜琴声还是透过书房传了进来。
埃丝特 你真让人心疼。真的,维克。(向他走去,但他做了个看手表的动作,抗拒她的关怀)
维克托 我得另找家具商。走吧,我们出去吧。(努力表现得高兴,却显得筋疲力尽、徒劳无功)咱们去洗衣店取我的正装,扮一回富人!
埃丝特 维克,我不是说我——
维克托 算了,别再说了。等一下,让我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别让人顺手牵羊。(他拿起花剑和面罩)
埃丝特 你还会击剑吗?
维克托 (他的悲伤和冷淡都挥之不去)哦,不行,击剑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很高,发力主要靠腿部力量——
埃丝特 让我见识下呗,我还从来没见过你击剑!
维克托 (退让一步)好吧,不过我下蹲没法蹲到位了。(他站好,调节好双脚角度,上下几次,找到合适的位置,颇为困难地半蹲下来)
埃丝特 也许你可以把这项运动重新捡起来。
维克托 哦,不行。太消耗体力了,这可是世上最难的运动。(重新站位)好,站那儿别动。
埃丝特 我吗?
维克托 别怕。(抖动剑尖,噼啪作响)这是把好剑,看它多灵活!我用它打败了普林斯顿。(他疲惫地笑了笑,从几码外大步冲过来;剑头碰到了她的上腹)
埃丝特 (向后跳开)天!维克托!
维克托 怎么?
埃丝特 你看起来真帅!
[他笑了,既吃惊又有些尴尬。这时,从外面走廊上传来一阵持续不断的响亮的咳嗽声,他俩的注意力都转向了门口。咳嗽声更响了。
格雷戈里·所罗门走上场。总而言之,这是个令人称奇的人物:年近九旬,却仍然腰杆笔直,气宇轩昂,以一种完美的方式倚靠在自己的拐杖上,看起来丝毫不显体弱。
他头戴一顶破旧的黑色软呢帽,像吉米·沃克[20]那样把右边帽檐儿压低,不过他这顶可脏多了。身上一件不成形的大衣。打着一个粗大的结的领带业已磨损,歪歪斜斜地躺在翘了角的领袢下方。里面的背心皱皱巴巴,裤子松松垮垮。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钻戒,腋下夹着一个破旧不堪的皮文件夹,胡子拉碴。
他仍然咳嗽着,想歇口气,一边努力却徒劳地试图像商务人士那样拂去上前襟的烟灰,一边朝埃丝特和维克托点头,举起一只手示意他这就开口。他瞥见了维克托手上的花剑,露出不无怀疑的神情。
维克托 我给你倒杯水好吗?
[所罗门傲慢地摆了摆手,拒绝了他,试着止住咳嗽。
埃丝特 你还是坐下吧?
[所罗门打手势表示感谢,在舞台中央的扶手椅上坐下,咳嗽声渐渐平息。
你确定不来点水吗?
所罗门 (操着俄裔犹太人的口音)水就不用了,我可以用点儿血。谢谢。(他深呼吸几次,注意力转向维克托,维克托放下花剑)好家伙,那些台阶可真够呛。
埃丝特 你现在好点了吗?
所罗门 再多几级台阶就能上天堂了。啊——打扰了,警官,我在找一个客户。名叫……(他的手开始在背心口袋里掏摸)
维克托 弗朗茨。
所罗门 对,弗朗茨。
维克托 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