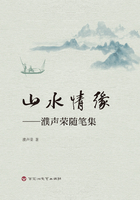
家在永州
家在永州。永者,二水也。潇湘二水在此汇流。
零陵县城位于潇水东岸,城之四周都有城门。与西门相对的潇水西岸有一支流汇入,名曰冉溪,柳宗元将冉溪改为愚溪,并在其居所周围,修建了溪、丘、泉、沟、池、亭、岛等八景,在其前都加一愚,于是就有了“八愚”。
沿愚溪上行50里,即是愚溪源头——大古源,即是我的家乡,我的出生地。严格来说,愚溪源系越城岭北山麓下一系列泉水汇集而成,包括戴花山、小桃源、大古源、鼎仙观、龙角井等泉水,我家西侧的腊树井,我外婆家坝塘里井泉皆为愚溪的源水。以大古源泉水流量最大,平水期的流量可达1立方米每秒以上。鼎仙观的岩泉系一喀斯特伏流(暗河),距我家不足一里,位于黄家岭山脚下,鼎仙观庵子(20世纪50年代初被毁)门前。泉水一年之中变化较大,丰水期流量可达1~2立方米每秒,枯水期仅几十立升每秒,甚至成为涓涓细流。该泉下流成溪名曰梅溪,从我家屋后绕过,成为我家洗衣、洗菜之用。
鼎仙观暗河水是我家屋后数百亩稻田浇灌水源。由于该泉水丰枯期间变化较大,故在我家西侧有一水塘,叫荷叶塘,水面宽50亩左右,容积不足百万方。春夏之交,雨水丰沛之时,引鼎仙观岩溶水灌入塘中,作为农田灌溉和洗涤之用。夏秋时节也是少年儿童戏水玩耍的乐园。
这一系列泉水的形成,主要是五岭山脉雨水的补给。泉水清洌甘甜,毫无污染,水温冬暖夏凉,可以直接饮用。每年夏季时节,毒日如火,中饭后,大家常到后头屋里几棵大古树下乘晌午凉,大人们谈白(闲谈),议论庄稼禾苗、天气好坏,也常谈一些古话轶事、乡间趣闻。男人们一般都穿一条短裤,被晒成古铜色的上身,赤膊着,肩膀上搭一条一米多长的洗澡帕,除了晚间洗澡擦身之用,白天主要用来擦汗。男人们一般围坐在中间,妇女们一般在旁边,且多是男的说,女的听,有时也有年长的奶奶婆婆成为谈话中心。有时长者发话:“耐(热)得很,挑担井水来吃一下。”这时那些勤快的女孩或年轻的媳妇,会爽快答应“我去”。她们回家挑起水桶并带上水瓢去腊树井眼或坝塘里井眼挑一担井水回来,两处距离都不足一里,来回不到一袋烟功夫。小孩们往往是抢着喝,之后是男人们喝,最后是女人们喝。而道仙公公喝水时,总有意问一句:“换肩没有?”答道:“没换肩!”
对外地人来说,这一问一答,肯定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首先要搞清“换肩”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家乡,搬运重物一般是挑或抬,挑东西一边肩膀挑久了,要换到另一边,让左右肩轮换休息。道仙公公问“换肩没有”,是有点名堂的。如果你没有换肩挑来的水,他就会去舀前面的一桶水喝,后面的那桶水他认为挑水人肯定放了屁,污染了井水。大家都知道此老人的毛病,即使在路上换了肩,也说没有换,图他一个高兴。
鼎仙观岩门泉是一喀斯特暗河出口,少时放牛砍柴常来这里,特别是夏秋季节,溶洞大约数十米,靠近洞口处,有龙王菩萨,沿水流往里走百余米,溶洞变得狭小,行走困难。据说这个溶洞有几十里,洞中有巨蟒,有人见过,我们倒见过洞内深处有许多蝙蝠。水流一年四季变化较大。四十年前村里在山口外筑一土坝,想蓄水,调节水量用于水田灌溉,但溶洞很多,蓄不住水。村里叫我去看过,表面溶洞很发育,覆盖层很薄,处理工程量大,故大坝筑成后,一直没有发挥作用。
大古源泉水下面也修有一水库,情况同此差不多,也蓄不住水,处理工程量大。一直为一干库。我中学同学黄朝鸿在此当公社书记时,叫我去看过。
上述几处大的泉水以及大大小小的多处泉水、溪流汇合后东流50里至愚溪口,注入潇水。
我家屋后大山即为五岭山脉越城岭,往东南延伸即为萌渚岭、都庞岭,基本都为泥盆纪沉积岩石构成的峻峭的中高山,多为石灰岩构成,而大山之下都为馒头状的丘陵山包,相对高差三五十米,少数仅一二十米。构成这些山包的岩石有两类:一为红色砂泥岩,一为石灰岩,前者质软,相对隔水;后者质硬,由于溶蚀作用形成各类溶蚀孔洞,称为喀斯特地貌,桂林山水地貌即是。由于灰岩透水而泥岩隔水,故在两种岩性交界处,形成喀斯特泉而涌出地表。在我们这一带,泉眼很多。在坝塘里我外婆家就有不少泉水井,在路边的井眼泉水平常流量在0.5立方米每秒以上,在我九妹外婆的灶房下边的泉水井,其流量也有四五十升每秒。而外婆家与九妹外婆家是连着的,到泉水井不足10米,因而,外婆家是不需挑水饮用,而是拿一个水桶到井眼里提水饮用。
有时我在外婆家,恰巧外公在外做事(干活)回来,外婆就会叫我:“宝崽,快到井眼里,给你外公打箪水来吃!”箪是用来舀水的竹筒,可装一两斤。于是我就跑到井眼舀一筒水拿给外公喝。一般都喝泉水,只有客人来了,才烧水泡茶招待客人。我在家干农活时,特别是阳春三月创草皮烧土灰或沤田时,半晌午饿了,如家中锅里有剩饭,就舀一碗,用井水一泡什么腌菜都不要,呼呼几下,吃完,继续去挖草皮。
那个时候,肚子没有油水,特别容易饿,一餐吃一斤米饭,可以说笑纳。特别是五黄六月,新谷没有下来,而事多活重,且常常要吃一些加南瓜豆角做的麦子粑粑,或者吃一些把大米磨碎熬的粥,再加一些南瓜、豆角等蔬菜。我的奶奶就是中午磨碎米时,突发脑溢血而去世的,时年57岁。
在愚溪入潇水处建有一码头,与对岸的大西门相对。历代过河坐渡船,至上世纪初,人们用船搭成了浮桥,过河非常方便。但河流要运木头,为了木排通过,每天下午2~4时要拆掉浮桥,让木排通过。另外,就是汛期河里涨大水时,也要拆掉浮桥,过河靠船。此时坐船水大浪高,比较有风险。我记得有次我有个表叔对我父亲讲:“前次过河时,我把鞋子的带子和衣服的扣子都解了。”言下之意,万一翻船,可以很快甩丢鞋子和脱掉外衣,游泳逃生。一般来说,南方的男人基本都会游泳。但也常听到这样的话:淹死的都是水幺子。即都是会游泳的人。
给我家寄信的地址有很多地名:最早写三坵田,后是梳子铺,或写荷叶塘,这三个名字都要写濮家。家乡的三坵田或梳子铺很有名,远近人都知道。知道荷叶塘的却不多。从我记事起,家门口的水塘很大,但从未见过荷叶荷花和莲藕。水塘装满水时两三米深,最深可达四米左右。夏天这里是我们少年儿童中午嬉戏的天堂,吃完中饭放下碗筷,就跑到塘里去游泳。少年伙伴常玩的游戏有两种:一是爬到塘埂上的树枝上往下跳;二是潜到水底抓塘底软泥巴,再浮出水面打泥巴仗。打泥巴仗要会踩水,上半身露出水面,再用手里的泥巴砸对方的头,对方则要躲避,头潜入水。一般分两派。有时打得死去活来,眼睛、耳朵都是泥巴,眼睛红肿几天。这种愚蠢的游戏,带给我们的却是难以忘怀的快乐。
荷叶塘虽不产荷花莲藕,但可以养鱼。因为水塘是我们濮家屋里的,过去是大家出鱼苗钱,推举人来养,春节时捕捞,给每家分鱼。春节前抓鱼是非常壮观的场面。前几天就放水,放至水深1米之内,然后每户出一人用竹子织的竹排沿着塘底把鱼从一边赶至另一边,逐步缩小到一定范围,再用罾把鱼捞出来。在捕捞过程中,鱼有时从竹排缝隙中,或排底钻出来,这时跟在排后面的用虾笆,往往会有意外收获,能抓到漏网之鱼。有一年我跟在竹排后面,虽然没有抓着鱼,却踩到一只团鱼(甲鱼),当时我不敢捉,怕被团鱼咬,还是叫外公来逮着的。
干塘抓鱼的气氛很热闹,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虽然塘水的深不到一米,赶完塘全身湿透,一身泥巴,特别是小孩们。南方的水虽然不会结冰,但估计也是4~5度左右,还是相当冷,但人们不在乎这些。
干塘后,濮姓家族每户都可分到一些鱼,分鱼是按户,大小鱼及种类搭配,然后编号,抓阄分鱼。一般除留下自己吃的鱼,还要给亲戚们送一些。
七八十年代以后,塘里养鱼采取私人承包方式,承包人每年给生产队交多少鱼或多少钱,不再分鱼,干塘抓鱼再没有往日的热闹了。
在越城岭山麓下,三座名山之间的广大空间,是一片丘陵、岗地,丘陵之间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田垅,这里就是养育我们一代代子民的乐土。丘陵山岗一般都栽有松树、杉树、油茶(籽)树。还有矮小灌木、蕨类、茅草,一般砍来做柴烧。
少时,放牛就在这些丘陵山岗间。我们荷叶塘村有着彭、黄、濮、宋四大家族,各族放养牛的方式各有不同。我们濮家是各放(养)各的牛,谁也不管谁;坝塘里黄姓外婆家,则往往是合伙放养,早饭后,将十几条牛,赶往大山里,如不需牛劳作,放养几天,才把他们从山里赶回来。彼此的牛都认识,并且牛也认识自己的主人,喊叫几声,则可把牛叫到自己跟前。我们虽然各放各的牛,而一到山里,牛就合到一起,这时只要一两个人拦住去有庄稼地方的路,任它们往山里去吃草,而小伙伴剩下来的事,就是:耍。
开春后,牛就辛苦了,牛要犁田耙田。一般是上午放养牛,让牛去吃草,主人则把牛、猪粪肥挑到田里,撒好肥,下午则让牛来耕作,直至天黑。
有时时令紧,忙不过来,清早就赶牛去犁田,直至吃早饭。然后让牛去吃草、休息。中饭后,再让牛来耕作。黄牛一天只耕田一亩,大的水牯牛可以耕两亩以上。
农家田不多的人家,也有两家合养一条牛的。轮换放养,平时一家放养一月,忙时一家一天。谁放养牛,谁得牛肥。肥料是稻谷生长的基础。过去没有化肥,主要靠牛粪、猪粪以及鸡鸭粪。所以,一般农家种田耕地,必须养牛、养猪、养鸡鸭,不仅可以吃其肉,还可以肥其田土。
解放前夕,我家一段时间没有养牛,是外公家的牛替我们耕作,因而,也没有牲畜肥料。往往要去排龙山小学,购买人粪尿。买人粪尿按担计算。故买者往往挑一担很大的粪桶,把粪挑出大门外后,在背地里,再匀做两担挑回来。
除粪肥外,我们这里还经常使用两种肥料。一种是绿肥,就是树的枝叶或矮小灌木的枝叶,一般在冬季把它砍下来,沤在冬水田里,作为肥料;一种是烧的土肥,就是山岭丘陵间树下生长的草皮,连土带草创下烧成灰。在这些灰中添加一些人粪尿,混在一起使用。多用在旱地,种麦、种豆及种蔬菜,有时也用在水稻田里作追肥。
在山野间创草皮烧土灰,往往是前几天,把草皮创下,把它晒干,然后堆集起来,点火再烧,一般要四五天,甚至七八天才能把它烧透,成为熟土。再过几天,等灰土凉了,打碎成土灰,就成为肥料了。
我八九岁时在家放牛,除专门放牛外,还兼给牛割草,拾些柴禾。与放牛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做过一些有趣的事,甚至荒唐的事儿。
春天,谷雨过后,天气转暖,满山都是生机勃勃,最早开的花是万紫千红的杜鹃,然后是金银花,再后是油茶树花。一旦茶树开花,通常我们折一根蕨枝,抽去中间的芯,就是一根很好的吸管,然后去吸取茶花中的花蜜,花蜜凉甜凉甜,味道好极了。茶树上还会结出一些“茶耳”“茶泡”,茶耳如人的耳朵,白色,如油炸的虾片;茶泡为乒乓球大小,亦为白色,茶耳、茶泡可以吃,而且非常好吃,甜丝丝、脆生生的。但不是每棵树都长,仅有少数树生长这稀有的水果,至今我也搞不明白它的生长规律。
在放牛期间,我们也偷吃自己地里的红薯、花生,以及栽在田埂上的瓜果,如黄瓜。一般是轮流去挖,去摘,一家搞的多了,大人发现会骂的。
在冬天,我们有时会去水田里摸鱼。这是人家放养在水田里的鱼,有鲫鱼、鲤鱼,是养在稻田里,割禾时特地留下来,准备留做过年吃的,或准备留做鱼婆做种的。抓住鱼怎么吃?就是利用山岭里烧土灰的阴火。一般用桐树叶子把鱼包住,外面糊一层泥巴,埋在还在燃烧的灰堆里。头天埋进去,第二天出来放牛时,扒开,取出来吃。有时还约定××从家里“偷点”盐出来,则烧鱼的味道更鲜美了。
我们放牛时,还见到过讨饭的叫花子,偷人家的鸡,在灰堆里烧着吃的情形。叫花子偷鸡很有诀窍的。他们把玉米粒或黄豆用水泡胀,用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线(用地里栽的麻,剥皮撕开,搓成麻线),穿上几粒,一头绑上一根树枝,在人家屋后,没有人的地方,把带有吃食的线撒出去,鸡一旦吃下,抓鸡则手到擒来。鸡还不会叫,抓住鸡用布袋一包,把鸡头用力一扭,鸡就会无声无息了。叫花子会找一个有烧土灰的山野间,把鸡毛拔掉,从灰堆中弄出火星,点燃柴禾,烧光鸡身上没有扒光的鸡毛,然后,开膛剖肚,只要鸡肝,丢掉其它内脏,用桐树叶把鸡包住,外用湿泥巴糊住,扒开灰堆,放在灰堆中央有火星的地方,再用有火星的灰土将其盖住,第二天清早,前来取出,成为他一天的美味。
据说,西湖的“叫花鸡”就是这么来的。我小时吃过“烧鱼”,但没有吃过叫花鸡,只吃过“盐老鼠”(蝙蝠)。在鼎仙观的岩洞(溶洞暗河),往里走近百米,溶洞变小,人难以行走,蝙蝠就躲在里面。它们白天是不出来的,天黑后,它们会出来觅食,受了惊吓,它们也会飞出来。抓蝙蝠的办法,一个人往洞里走,扔石头,并大声吼叫,蝙蝠受到惊吓会飞出来。这时,在外面不远处,站几个人,手拿毛竹刷子(毛竹枝杈),左右使劲飞舞,往往会打下一些,落在地面上,把它弄死。再从嘴部把它撕开,连皮带翅膀撕掉,只要中间一团肉,也不要内脏,用水冲洗干净,和烧鱼一样,用桐树叶包好,糊上泥,埋在有火的灰堆里,第二天放牛,扒出来吃。开始我不敢吃,以后尝了尝,味道真不错,与麻雀肉无异,据说吃了还明目。
稍大,我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力,不要我去放牛,而要我去做正儿八经的农活了。一年忙到头,春天创草皮,烧土灰,然后犁田,耙田,插秧;夏天在稻田媷草,撒石灰,还忙地里活路;秋天收割,秋种;冬天砍柴,烧石灰。春夏季节,农事最多,也最忙,活路也最重。夏秋双抢时节,太阳毒,时间紧,早出晚归,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就是我的少年生活。
当我外出读书、工作时,这些农活全部都落在了弟妹们身上。对于他们的辛苦,我是深有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