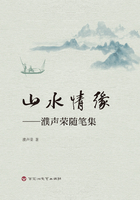
母亲
我有两个母亲:生母龙满秀,我8岁时,就得了肺病去世;继母盛宝雨,我八岁半时,她与父亲结婚,我们在农村共同生活了近10年,直到我去长沙读书。
满秀妈妈也有两个母亲,也就是说,我有两个外婆:里洞龙家外婆和坝塘里黄家外婆,我习惯叫龙家外婆和坝塘里外婆。
母亲在龙家外婆那里是“满女”,在坝塘里外婆这里更是“宝仔”,看得比男孩子还重,虽然家中不富裕,但像当小公主一样,生活自由而快乐。
母亲在外公外婆的影响下,从小勤快能干,上山砍柴、打猪草、放牛、种菜、插田割禾都是一把好手。母亲性格倔强,争强好胜,做事从不服输。农村妇女一般没多少文化,而我外祖父母较为开明,送母亲上完了小学,觉得有点文化,今后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好处。
母亲对社会的复杂、生活的艰难、农村的清苦,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做事十分发狠。我六七岁时,她就常在我耳边说,一个人只有靠自己,靠天靠地靠菩萨都靠不住。家里穷了,爹娘老子都靠不住。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她就要我跟大人去做事。外婆对别人说,我母亲上山砍柴,回来时还要德根“挑两个煮粑粑”(即两小捆柴)。外婆说我母亲:“孩子太小,莫要他去干什么活。”但母亲不同意这种观点,母亲回答是:“从小不吃苦、怕吃苦,长大了只有当叫花子”,“吃穿怎么来?是自己做出来的,好吃懒做,将来不会有出息”。
我小小年纪,正是玩耍的时候,但母亲要我干这干那,总不得清闲,我很羡慕邻居家的孩子,比我耍的时候多。
有限的一点田和一点地,在外公的帮助下,母亲侍弄得很好。加之后来父亲在邮局工作,有一份不错的薪水,我们家中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母亲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冬天事少时,她上山砍柴,家里堆下一大堆,有时还会挑柴给外婆家烧。家里有了好吃的,如杀了鸡鸭,或在圩上买回一点肉,做好后她都要留一点给外公外婆吃。这时外婆会说,留给小伢仔吃嘛,他们要长身体。但母亲会说,小伢仔长大了有吃的,能吃饱饭就行了。
母亲性格倔强,但待人谦和,宁可自己吃亏,也不占别人便宜。尽管外祖父母家境清贫,但凭自己劳动,为人处世,很受当地人尊敬。据外婆讲,母亲勤快,做事麻利。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父亲当时没有工作,祖母虽给父母分了一亩多田,尽管母亲做事发狠,但毕竟田少,生活艰难。父亲考取衡阳邮局工作后,情况才有所改观。母亲带我们在家,省吃俭用,不出几年就攒钱买了一亩多水田,在外公的打理下,基本解决全家一年的吃食。
后来母亲带我和维弟去了衡阳,同父亲一起生活了几年。家里的田都交给了外祖父母耕种,收成都归他们,也算是父母对外祖父母的一份孝顺。
我8岁多,母亲因肺病去世了。当时我还不懂事,没有哭。总觉得母亲对我太狠心了。光知道叫我做这做那,没有耍的时候,不像别人家孩子。外婆哭我母亲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德根不哭你啊!今后他哭的日子无眼泪!”意思是今后有他哭的!
母亲还是很爱我们兄弟的,当她病重,有气无力对我奶奶和外婆说:“原想苦几年,给德根德维俩兄弟买几亩田,将来好有饭吃……,但阎王不留人啊!”
尽管我对生母有“意见”,但在母亲的影响下,知道在农村干活是天经地义的事。干活,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好的道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根很深。
当我六岁、维弟两岁时,母亲带我们去衡阳,与父亲在一起,我在那里读了近两年书,以后母亲生病,我们就回到了乡下。
宝雨妈妈是我继母。生母去世后,我与维弟住在坝塘里外婆家。时间长了,祖母觉得我俩兄弟长期住在外婆家不合适,就接了回来。带两个孩子不容易,我还要读书。所以,当父亲与继母结婚后,祖母叫人把我兄弟俩送到衡阳,与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但不到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父亲不愿在衡阳邮局工作,带我们回到了乡下老家。
我与维弟原来就在农村,对农村生活是习惯的。但宝雨妈妈一直生活在城市,且家境较好,她是父母的宝贝女,上有兄长呵护,下有弟弟们的爱戴,父母送她上学读书识字,缝纫绣花,做得一手好女红。由于父母去世早,她成了一家之主,照顾兄,培养弟,费尽心血,所以,兄弟姊妹关系甚好。继母来到梳子铺老家,已年届30,以前在城市生活,虽不怎么优越,但衣食无忧。现在来到农村,吃的粮食和蔬菜需要自己种,烧的柴禾要自己上山砍,吃的水需要到井眼里自己挑。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是个考验。而我只有十来岁,维弟只有五六岁。父亲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小也没干过重体力活,既缺少力气,又不会干很多农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真苦了我的继母。
刚回来时,外公那里还有我们一点谷子,父母亲还有一点钱,生活还过得去,还有饭吃。最困苦的日子主要有三段:一是50年代初,我和父亲务农,后来父亲当小学教员,工资微薄,既要照顾我们一家,还要供养祖父母;二是1958年至60年代初,成立了人民公社,过苦日子,这时我已外出读书,父亲下放干校劳动,家中既无劳动力,又断了经济来源;再就是文化大革命混乱不讲理的时代,大家都过着苦日子,吃不饱饭,精神上还受打压,真是苦不堪言。
回到农村的第二年,苦难就开始了。首先是宝雨继母难产。因是大龄生育,又在农村,痛苦不堪,两天后抬到县城医院,开刀动手术,胎儿还未能保住,钱花不少还大病了一场。此时,粮食不够吃,吃杂粮、瓜菜代从此开始了。继母不仅要学着烧柴做饭,还要学着在地里种菜、养鸡养鸭,后来还出外打猪草养猪。农村这些事都要靠力气,往往没完没了。继母很坚强,挺过来了,对待我和维弟,虽不是亲生,她视如己出,非常慈祥,非常关爱。当时我年少,见我同大人般干重活,她很是心疼。特别是三黄五月,家里粮食紧张,吃饭时,她总是让我先吃,她对弟妹们说:“让你大哥先吃,他吃了要去做事。”有时候我回来晚了,给我留的饭菜总能让我吃饱。她自己总是最后吃,少饭少菜是常事。
继母手艺好。我们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缝制。特别是春夏换季时节,她去梳子铺扯上几尺布,为我和弟妹们做上短衣短裤,穿得漂漂亮亮,与同村儿童少年相比,我们多了几分自豪。她会织毛衣,而且可织出各种花样,在当时农村是非常稀罕的。她替别人织毛衣,可以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有时候可以换工,别人可以替我们做点农活。由于她待人谦和有礼,乡村邻里没有不夸赞她的。特别是坝塘里外婆,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心疼的不得了。而继母对外公外婆也是疼爱有加,百般关心。这也影响我和维弟兄弟俩,我从未把她当后妈看待。而我对我的弟妹们也从未另眼看待,如同一母所生,关系非常融洽。
60年代,是我们那儿最苦的年代。1960年我在长沙毕业,去陕西工作前,我回了一趟家。继母带着几个弟妹,在家过苦日子。虽然生产队已不吃大锅饭,可以一家一户自己做着吃。但分下的粮食很少,吃饭常加一些谷糠和瓜菜,冬天一天只吃两餐饭,且多以红薯、南瓜为主。继母还给我说了一件事,当时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生产队振根爹带人到我家里,用锄头把腌的咸菜坛砸了。真是可恶!自家腌的咸菜自己吃,怎么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家还是贫农啊!怎么做这种缺德事呢?文化大革命后不几年,振根爹一家不知怎么的,先死了儿子,后死了女儿,最后他夫妻两口也死了,剩下祖山园里盖的一栋屋空落在那里,房前屋后长满了茅草。村里人闲谈时说,恶人有恶报啊,干的缺德事,不得好死!
当年农村粮食产量不足,每年又分得很少,家庭经济来源有限,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继母过日子,计划和节约是出了名的。省吃俭用,从不浪费。养猪、养鸡、养鸭很少喂粮食。即使割了稻子,也不会专吃白米饭,一定要加上一些粗粮。冬天的红薯、荞麦,加一些当饭吃,往往是先吃红薯后吃米饭。夏秋季节,南瓜、豆角下来了,也要多煮些当饭吃。继母对我说,最艰难的日子,生产队给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全靠瓜菜,这种苦日子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然而,没吃几天饱饭,而我经济条件也稍显宽裕的时候,她却病了,得了半身不遂,还是受苦受难。
继母人贤惠,也富有同情心,与乡村邻里们关系都很好。前面已经提到,她与她的兄弟们关系很好,特别是与他小弟,嘉让舅舅关系很好,联系密切。小舅在解放前夕与他的女友(后来成了舅娘)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分配到广西工作至今。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接济我们,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帮我们度过了许多困难时刻,这是我难以忘怀的。
继母非常宽容大度。父亲退休时,没有让达弟去顶职,而让已在小学工作的维弟去顶职。据父亲说,继母对达弟说:“德维是你哥哥,他大些,让他去顶替吧,莫要跟他争。”(德维与我系一母同胞,这种大度非一般继母所能做到。)
达弟素来忠厚,几十年来,父母与他吃,他侍候父母几十年,毫无怨言,这与母亲的言传身教有关。我虽小时候吃过不少苦,但弟妹和父母比我吃的苦更多。十五岁后我离家外出读书、工作,从此,再也未能在父母跟前尽孝了,特别是对继母,她没有享受到我的福,为此我常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