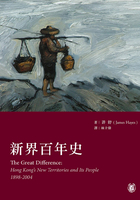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第二章
原有的英國直轄殖民地和「巨大差異」
英屬香港
現在我們來看看「巨大差異」另一頭的世界,亦即新界將會納入其疆域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在十九世紀到訪香港的西方人眼中,「香港」是指香港島,再具體點說,是他們所稱的維多利亞城,不過這個名稱主要見於官方文件,而非時人日常的稱呼。在1881年,乘坐英艦「酒神女祭司號」(Bacchante)環遊世界的兩名年輕英國王子來到香港,他們在海軍船塢上岸,入城後看到街道「寬廣清潔,街上滿是轎子或人力車,轎子有兩根竹製抬槓和綠色頂篷,兩側有藤編擋板。街道兩旁是意大利式有拱廊的巍峨白色房子,還有樹叢、林蔭車道,以及沿着山坡一路通往山上的行人道」。(1)城中歐籍人居住的區域,一向令外來訪客讚歎不已。在1878年,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女性旅行家畢曉普夫人(Mrs. Bishop)(2)形容香港是「東方最宏偉壯觀的城市」,接着又說:「氣象恢宏的維多利亞城沿着其南岸綿延四英里,城內有六千間以磚石構築的房屋,商人和官員所住的堂皇第宅和寬敞別墅,沿着山頂陡峭的山坡蜿蜒而建。說它是由蘇伊士運河出發的海軍艦艇和商船的終點,一點也不為過。」 (3)大約十年之後,一名到訪的英國國會議員寫道:「香港從燠熱的不毛之地,蛻變出世外桃源般的幽雅景緻,將永遠令世人讚歎。」(4)
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旅行家對這個地方尤其感興趣。在1878年聖誕節,審美眼光獨到的藝術家戈登——卡明女士(C. F. Gordon-Cumming)坐船駛入維多利亞港,她同樣大為讚嘆:「竟然來到如斯美麗的地方,是我意想不到的。它的美麗突然顯露,令我喜不自勝,一時間無法言語。」(5)霍華德·文森特夫人(Mrs. Howard Vincent)則形容它是「東方城市中最美麗者」,並以動人的筆觸描繪它在陸上和海上多姿多彩的生活。(6)足跡遍及全球的許布納男爵(Baron de Hübner)在1871年到訪香港,並留下有關這個地方的生動記述,他的手法頗為不同,他把香港比喻為「在一道電燈光照耀下,透過放大鏡觀看的文特諾(Ventnor)或尚克林(Shanklin)」。(7)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重建,寇松(Curzon)口中「世外桃源般的幽雅景緻」,今天已所餘無幾,但幸虧有照相機,並多得當時的攝影家和今天的出版商,我們還能夠一睹這個海港城市憑什麼贏得當年那麼多旅行家的熱情讚賞。(8)
維多利亞城的華人聚居區主要是向城的西面延伸,這個區域呈現極大對比,但同樣引人入勝。港督德輔(George Des Voeux)爵士在1888年形容該處屋宇是「按照中國特有的式樣建造,建築物料之堅固幾乎並無二致,但排列密集,擁擠地聚攏在一起,在這方面堪稱舉世無雙」。他接着說:「在維多利亞城某個不超過半平方英里的地區,估計有逾十萬人棲居。據說,每英畝的空間就住了一千六百人。」(9)十年後,一位署理港督在向定例局(10)發表告別演說,細數自己的功績,提到為城內華人提供休閒設施,協助撲滅瘟疫,說這些屋宇內有「一群臭氣沖天的人」,他們所住的房間「陽光永遠照不到,惡臭的空氣滯礙不通」。(11)在1902年,署理律政司形容華人房屋「與兔子窩沒有兩樣」。(12)
1898年時,絕大部分華人居民是流動人口,而且大多數是男性,自英國統治香港以來,大部分時間情況都是如此。(13)人民自由來去,而他們的去留是取決於就業市場、親友的意見,或者中國國內局勢。此外,有大量華人取道香港的港口往返中國。他們大多住在上述擁擠的大雜院式公寓或者臨時居所,基本設施同樣付之闕如,這或多或少是引發傳染病甚至大瘟疫的原因。這些人主要是工匠、店員、苦力(在海旁地區尤其多)和小販。這裏基本上是個男性社會,休閒娛樂都是以他們為對象。生活忙亂刺激,迥異於農村的恬靜平淡,而大多數人離鄉背井,可能就是為了逃避這種熬清守淡的生活。在多方面而言,雖然仍然身處華人土地,而且離故鄉很近,但他們的社交生活,和那些遠赴他鄉、生活和工作在非華人之間的同胞沒有差別。(14)
然而,除了這批稠密的黔首黎庶,到了1898年時,香港也有一批人數不多但生活優裕(少數是巨富)的華人精英。他們大多是商人和企業家,有些人還有英國國籍(自軒尼詩〔Pope-Hennessy〕出任港督的時代〔1877-1882〕起,就准許華人歸化英籍),並且很樂意以此英國殖民地為家。(15)有兩名華人當上定例局議員,另有一些人成為有影響力的董事會和委員會成員。那兩名定例局議員就是代表這群人,向當年前往中國考察商務,順道到訪香港的貝思福勳爵(Lord Charles Beresford)游說(詳下文)。(16)
這個殖民地還有另一個組成部分。對於這個部分,沒有人比金教授(Professor F. H. King)描述得更淋漓盡致,〔1909年〕3月8日一個多雲的晚上,他的船在離開香港前往廣州時:
……景色美得讓人驚嘆。我們正逐漸遠離三個城市:第一個是沿陡峭山坡而建、有電燈照耀的香港……;第二個城市是海港對岸的新舊九龍;第三個城市處於這兩者之間,與兩岸不相連接,它是在一大片空曠無人水域上的海中城市,由各種舢舨、中式帆船、近岸小艇組成。這些船舶按照警察規定,在日落後停泊在一起,形成一個個街區和街道,到了早上才又各自四散。(17)
住在「海中」城市的,是來自不同地方的水上人。這些人主要是說粵語的蜑家人,他們是廣東省的本地人,在維多利亞港提供駁運和載客往來服務。另一些水上人是來自鄰近福建省的福佬人,他們有些在本地定居,並從事相同的營生;有些則是定期沿着海岸航行通商和載運貨物,只是每隔一陣子途經香港,幾乎直至今天還有人做着這樣的工作。此外,甚至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有些工作不是那麼穩定的本地或外來漁船,有機可乘時就會幹起私梟甚至海盜勾當。(18)
這群居住在城市的芸芸眾生,無論在海上還是陸上,都是由一隊殖民地官員管治,並由英國人、印度人、馬來人和華人組成的警察輔佐,另外駐有一支由英兵和印度兵組成的龐大軍隊,有事時可出動協助。這個殖民地從一開始就以西式法律和行政方式管理,法庭通常不會採用中國法律和風俗,儘管它們在法庭以外或多或少還在使用。(19)
更具體地說,政府是沿用英國直轄殖民地常用的模式,總督由委任的議政局(20)和定例局輔助,兩局議員大部分是政府官員。施政方針和財政是由總督會同議政局決定,而他的決定經輔政司署傳達至各部門,輔政司署的首長是輔政司,他掌管一般行政事務。田土和建築、港口和海港、工務、警察和監獄、公眾教育等,則由一些專職部門負責。華民政務司署負責與華人聯繫,並且在華人精英協助下,為管理華人事務提供意見。(21)法庭採用英國普通法審理案件。(22)香港政府是個緊密的組織,非常適合管治幅員細小但人口稠密的領土。
這個政府有時候也很專斷獨行。事例許多,可舉一個1900年的例子以資證明。為了預防鼠疫,定例局通過一條潔淨局附例〔須得定例局批准才可成為法例〕,要求鄉村屋宇〔和市區唐樓一樣〕的屋主「在5月至6月和11月至12月,每年至少兩次」為房屋掃石灰水。後來經過何啟博士大力奔走,並得到另一位定例局議員協助,才推翻原本一致通過的投票結果。可想而知,此事在新界必會引起軒然大波。(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