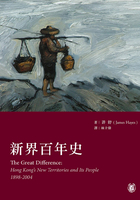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第一部分:農村社會
科大衛(David Faure)寫了一本關於新界東部鄉村與宗族的書,是關於香港地區聚居模式最詳盡的著作,他在卷首開宗明義說明構成地方社會的基礎:
香港的新界在都市化之前,這個地區是由一些聚落組成,這些聚落有的只住着單一群體;有的則由數個群體聚居,而這些不同群體內的人,全是追溯至一個共同祖先的後代。在英文文獻中,這些聚落通常稱為「鄉村」,而擁有着共同血緣的群體則稱為「宗族」。
科大衛接着細說這些他和其他同行學者使用的術語,解釋其複雜意義。(5)我此書並非那麼專門化的歷史著作,所以使用這些術語時,涵義較為寬泛。
在1898年的新界,宗族和鄉村都是所在多有的事物。宗族的規模由幾十至幾千人不等,而鄉村同樣差異很大,但新界七百條或以上(難免是粗略的估計)的古老村落,大多數人口不多,由五十至一百人不等。(6)許多鄉村是單一宗族的聚落,大、中、小型的都有,另一些則是多個宗族群居;但在西北方的廣闊平原,那裏的大宗族或聚居在單一的村落集合體中,或分成不同分支,在多個地點建立類似的村落集合體。(7)無論建立的歷史長短,本地聚落都是緊密簇集,屋宇擠靠在一起,有些建在有圍牆的村子裏,有些則是在沒有圍牆的長方形封閉地帶之內;又或者背靠高地或山坡,成一列或多列的佈局,據1930年代到訪中國的人形容,它們猶如「為求安全而挨擠在樹籬下的羊群」。(8)大部分農村建築都有防衛作用。見圖三和圖六。(9)
定居的時間也長短不一。在1899年時,最大的本地宗族在新界已世居近九百年,而許多較小的宗族也落戶至少幾百年。(10)從族譜所見,這些宗族全是在這段長時期陸續遷到這個地區,除了十七世紀中葉的清朝初年,那時候,初入主中國的統治者為斷絕宿敵(11)所得的接濟,強令中國沿海地區居民遷往內陸,新界也不例外。(12)在那時之前,遷入此地的移民主要是粵人,或者長期以來已被這個主流群體同化的土著。後來,為了填補因厲行遷界令而減少的人口,客家人在官方鼓勵下大量移入,在1840-1860年,又有另一波來自廣東東江流域的移民潮。到了英國租借新界之時,客家人已佔陸上人口將近一半。(13)
開基祖若是落擔在空置和沒人開墾的土地,要立足並不困難。根據這個縣的風俗習慣,他們可能須向某個在當地或外地的地骨主納租(或繳租給某個正在擴張勢力的新興宗族,這個宗族徵收地租,卻未必真的擁有土地業權),但這並非他們安家落戶的重大障礙。(14)為了更有能力應付未知的情況,幾個家族可能聯合起來,或者不同宗族的男性結拜為異姓兄弟。落地生根之後,把父母和祖父母的骸骨遷葬到新家園是常見之事。
新來者若是來到已存在的村落,問題就比較大了。他們通常要住在村外,直至獲得接納,那可能需時多年。他們還須面對一個情況,就是在附近山頭割草伐薪、放牧之類的權利,已經被各個村落或者村內的家族瓜分了。(15)
這些宗族來此定居之後幾百年間,有些孳蕃茂盛,權勢赫赫;有些卻人丁不旺,一代一代凋零;還有一些則完全消亡。(16)落戶定居之後的幾百年間,那些人多勢眾和野心勃勃的宗族,彼此的財富消長變化,難免會鈎心鬥角,互相爭雄。(17)無論在什麼層面,宗族和家族(而非它們的個別男丁)都是社會組織的重要元素。(18)
這個地區的歷史十分動盪不靖。(19)來自土匪或海盜的外來威脅很常見。在1810年前二十年間,海盜為禍尤烈,那時候龐大的海盜船隊侵擾珠江三角洲沿岸,1840-1850年代又再度肆虐。(20)同時,有些本地村落因入海為盜而惡名昭著。(21)內部方面,村落之間常結下宿怨世仇,還演成械鬥,這些村落械鬥往往持續多年,衝突中會有人命傷亡,房屋莊稼被毀。引發衝突的起因不一而足,但在這些農業社會,不外乎獲取和保護珍貴的灌溉水源,以及爭奪橫水渡和街市等經濟資產的控制權。(22)居住地點和祖墳的風水,也是觸發紛爭的常見原因,因為大家都相信選址可以左右禍福興衰。高明的堪輿本領極受青睞,因為可以用來破壞其他村落、宗族、房派或家族的風水,甚至逼走較早落戶定居的人。(23)如果紛爭嚴重,打鬥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死灰復燃,有時候因一些小事,就引發醞釀已久的仇隙。(24)在權豪勢要的大宗族支配的地區,受這些宗族箝制而無法自主的村落心感不忿。(25)甚至連散居此區域各處的大宗族各支系,彼此也會爆發械鬥。(26)有些宗族因好戰而聲名狼藉。(27)村落廟宇內所放的鑄鐵大鐘全刻上「國泰民安」,但這幾個字所反映的,似乎是希望多於現實,如夏思義(Patrick Hase)所說:「太平的田園生活素來是天賜福氣,但只能偶爾得之,而無法久享。」(28)地方民眾的所作所為若過於肆無忌憚,當局偶然會嘗試遏止,但也無濟於事。(29)
在個人和村落盛衰的背後,蘊藏着許多豐富的故事。有一些流播至今,經過代代相傳還添枝加葉。比如,據說林村谷的繁榮是由觀音山影響,觀音山的名字雖然聽起來感覺很慈祥,但這座山其實是一隻公雞,觀音山的山麓有兩塊大石,一塊疊在另一塊之上,恍如碾米的石磨,公雞就在這兩塊大石上吃掉村民的稻米。根據當地傳說,林村可以享三代繁榮,之後就會被公雞吃盡。(30)另一個故事來自毗鄰八鄉的元岡村,這條大村落有座失修荒圮的北帝廟,我就是在廟址聽聞這個故事。據說,這座廟是由勢力龐大的鄧族為破壞此村風水而建。從周圍的山頭看,元岡村形狀如龜,而龜以長壽著稱,鄧族在龜首建廟,用意是扼殺這個原本可以長存的聚落。經過了幾乎二百年後,在1922年有人(可能是風水師)道出箇中底蘊,於是村民將廟遷到今天所在的位置重建,(31)1972年時還加以修繕。(32)
有些故事可以上溯至非常久遠的時代。一個這樣的故事是說,在十三世紀時,皇帝賜封食邑予某人,命其浮木鵝於海中,隨其所至,以定所獲土地的界線。另一個故事述說在十四世紀末時,一個權勢赫赫的本地宗族(33)被明太祖抄家滅族之事。(34)
在村之上有鄉,傳統上,鄉是村落為守望相助而結成的集團,並在儀式上共同抵禦禍患——包括壞人和邪祟。一幅在租借初期繪製的地圖,顯示出當時「新界」各分區的名稱和範圍(圖四)。(35)這些分區約有二十七個,有各自的名稱,並且被人以不同用語來描述,(36)但大體上是指相同的東西,而且在十九世紀末,它們肯定具有地方自治組織的形式,在有需要時可以隨時運作,以促進共同福祉(也可能是為促進野心勃勃的私人利益)。大宗族(到此時全是廣府人)同樣有能力動員族內成員、佃戶或附庸村落(client settlement)的村民。1899年英國人接管新界時遭遇的武裝反抗就是明證,如裴達禮(Hugh Baker)所說,當時「全是由五個〔大〕氏族的士人策劃,並由他們傳達消息」,就是剛才提到的地圖上所見的Un Long District(元朗區)居民。(37)
除了「鄉」,還有「墟鎮」,各墟有各自參與的村落圈子。(38)新界最大的兩個墟是在大埔墟和元朗墟,定居於附近村落群的鄧族,在幾百年前獲得於當地設墟的權利。(39)另外也有一些小墟市存在。這些陸上墟市全按照固定的墟期開市,墟期之間是所謂「寒天」,即不開墟的閒天;新界幾個繁忙漁港也有特殊的墟市,最大的一個在大嶼山南面的長洲。這些稱為沿海市集就最貼切,它們每天開市,以滿足水上和陸上人口的各種需要。(40)這些墟鎮為農民提供服務,可以買賣貨物(那時候做買賣的大部分是男人);另外,想要討老婆的話,也多半是透過一個「中間人」網絡在墟市地區內尋覓和打探,這些中間人大多是來自附近鄉村的婦女。
墟市很有意思還在於另一個較不明顯的原因。三十年前我參加一次鄉議局晚宴,與擔任鄉事委員會主席的鄧合雲有過有趣的討論,令原本很尋常的飯局為之生色,鄧老先生告訴我,在他的青年時代(他生於1914年),從一個人的說話就能知道其來歷,因為當時各墟市區域之間的語言差異,仍然普遍清晰可辨。(41)鄧先生說,由於交通不便(往來旅行大多靠徒步)和地方團結精神造成的隔閡,形成這種語言上的分殊情況。(42)即使到了1950年代我在新界工作時,新界不同地方的粵語仍有明顯差異,而在1960年代末,兩位剛到新田和廈村開始做研究的重要海外人類學家,也有相同經驗。(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