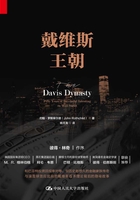
唯一一次债券胜出股票的十年
在大萧条之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大萧条的罪魁祸首是贪婪和资本家永不满足的欲望。在成立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简称证监会的听证会上,华尔街的银行家被嘲讽为只知道进行自我倒手交易,损害公众利益而自肥的家伙。从这些指责里人们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原来股市是一场庄家操纵的游戏,参与者像傻瓜一样被消灭。于是,投资者找到了另一个可爱的新投资对象:债券。
20世纪30年代是唯一一次债券胜出股票的十年。事实上,只有一种债券将投资者放在了安全的、成为赢家的轨道上:美国国债。公司债券复杂多变,很多公司深陷困境,无法支付利息。由狂热的经纪公司销售给美国大众的大量拉丁美洲债券(这是美国投资者首次被海外投资唤起热情)集体违约,只剩下容易上当受骗的投资者两手空空,血本无归。但是美国国债——沃瑟曼家族的最爱——为投资者提供了可靠的收入来源,取得了惊人的回报。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非由于国债本身表现杰出,而是由于其他债券的表现实在太糟糕。在稳定的滚动利率情况下,政府债券可以保有价值,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消费品、房屋以及其他任何用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包括股票,都在跌价。如若1932—1935年的危机重演,哪一个股票投资者不希望成为这样债券的持有人?而像沃瑟曼家族这样的债券持有人都以自己不是持有股票而倍感荣耀。
在重新思考30年代的危机时,戴维斯发现众人贫困的真实原因与通常推测的有很大不同。在凯瑟琳哥哥的公司工作期间,他研究了大量公司的起起伏伏。现在,当着手于更大的宏观社会背景研究时,他发现导致1929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企业的唯利是图。戴维斯认为,对于工厂“奇怪的停滞状态”,消费者不购买鞋子、衣服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这种现象,政府应该承担更主要的责任,而不是华尔街。不可否认,是莫名其妙的、高高在上的无法支撑的股价导致了大危机,是美联储1929年的加息打击了牛市。但是,如果是贪婪的资本家引发了大萧条,就像华尔街批评家们不厌其烦争论的那样,那么,英国经济状况所呈现出的不同,又做何解释?
正如戴维斯观察到的,美英两国的股市都崩盘了,但是当美国经济在整个30年代步履蹒跚之时,英国的经济产值却在真实上升。相反,在20年代,当英国经济徘徊不前时,美国经济却滚滚向前。对于这种跨越大西洋的两个经济体的盛衰易位,似乎最为合理的解释,戴维斯认为是投票箱。20年代,重商的共和党主政;30年代,反商的民主党取而代之。而在英国,20年代是反商的自由党主政,30年代是重商的保守党取而代之。无可否认,尽管这种结论过于简单,但戴维斯的确看到了政策和监管的浮躁如何将一场股市之灾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回到美国这一边,戴维斯探究了是什么因素延长了危机的时间。罗斯福总统执行了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策略,大力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复苏。为了执行凯恩斯的刺激经济理论,白宫不惜重金进行一系列的国家工程,铺设公路、建筑大坝、翻新国家公园等。到了30年代末,很明显,这些措施并未奏效。
那么,罗斯福新政措施的问题出在哪里?政府支出越多,税收也就越多,戴维斯指出:“税收负担越重,私人投资就越受到抑制。”将常规税率和罗斯福新政的附加税率相比较,可以发现,1932年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阶高达56%,比1925年翻了一番。四年之后的1936年,最高税阶更是高达62%。1937年,又开始征收公司未分配利润税。戴维斯认为,这些税收沉重打击了华尔街。“企业打起了退堂鼓,”戴维斯回忆道,“资本也作壁上观。”1932—1937年股市变得混乱不堪。
按照戴维斯的看法,整个美国税法的结构设计都存在问题。它以零税率奖励那些市政债券的持有人,以如此的慷慨,吸引资金涌入州和地方市政项目,而这些项目则是靠市政债券支撑。无论是否有价值,政府的这些建设项目对于国家经济产值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私人企业给国家创造了更多财富,增加了产值,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发明了新产品。尽管资本主义有其相对的优越性,但私人企业的投资者在股票和债券上被课以重税,而公共事业的投资者却得以豁免所有的税收,这样说来,税法才是阻碍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
罗斯福政府一方面以极度活跃的国税局阻碍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发表反资本主义的高谈阔论威胁商人和投资者。戴维斯写道,国家的CEO们从来不放过任何一个在报纸上或广播里谴责“财富的罪人”和“有组织金钱的自私”的机会。在新闻界和白宫的口号中,利润是公众的头号敌人,被指责为世界痛苦和贫穷的根源,尽管后来利润又被奉为解救世界的良方。罗斯福总统的一位顾问,斯图尔特·蔡斯,曾在一份代写的关于新政的秘密备忘录中提到,在演讲和文章中如何使用一些“褒义词”和“贬义词”。“公众利益”是褒义词,“储蓄”是褒义词,它使人想起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利润”是个忌讳的词。
对于巨头、大亨们的抨击,在工会大厅里、在失业大军中进行得如火如荼,吓得企业家以及银行家更加收紧了手中的资金。那些本来应该创建新公司、振兴老公司的资金,都流向了政府债券或国债。所以,随着金融家对于金融的担心,尽管凯恩斯主义盛行,经济依然停滞不前。
除了恶性税收和罗斯福的高谈阔论之外,戴维斯还指出其他三个原因加剧了大萧条:(1)为庇护美国本土制造商,国会对国外产品征收巨额惩罚性关税。(2)外国货币贬值。(3)企业兼并。(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末再现的兼并风潮和多重货币危机,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激烈争论,上述三个原因仍然适用。)
企业兼并如何导致经济的萎靡不振?戴维斯做出了如下解释。大公司的兼并会产生规模更大的公司,直到各行各业被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通用电气、杜邦、通用汽车、美国钢铁)所主导。当这些巨人凭借自己的体量横冲直撞时,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小型公司只能苟且度日,勉强为生。仅仅就汽车行业而言,大批的汽车制造商(施图兹、雷欧、奥伯恩、霍普莫比尔、威利斯-欧弗兰、哈德森、帕卡德、斯图特贝克等)或以破产告终,或被更为强大的对手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