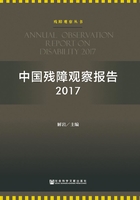
第二章 年度关键词
作为独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来自中国残障社群的我们,截取完整的自然年度即2017年1月至12月,使其“运动”,然后反复揣摩、循环论证、持续迭代,对照官方背景出炉的年度关联词,选择和确定中国民间残障领域的词语,并以“关键词”命名之,借此记录和呈现残障社群的关键节点,试图勾勒和阐释出一个个鲜活的中国残障者形象,并诚意期盼未来某一年“关联词”和“关键词”可以合并,实现官方与民间的关注议题趋于一致。
老残游记
文/蔡聪
2017年11月6日,中国残联举办“残疾人文化进家庭”发布会。会上宣布由相关企业赞助的7000万张旅游年卡将发放到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手中,凭卡可实现全国500家知名景区的免费观光旅游。这一官方举措一时间引发讨论不断。
不管是同情还是权利,在认知里,残障人都应该共享社会文明发展成果。然而在现实中,残障人能出门旅游吗?残障人出门怎么旅游?残障人出门旅游能游个什么?这些一直是包括残障人在内的很多人迟疑与犹豫的问题,也是很多残障人个体与组织尝试与探索的方向。
从别人有我也有、别人行我也行开始,这些年,我们看到了不少充满勇气与梦想的残障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出现在名山大泽之畔、月落日出之交,到慢慢地在诸多需要协调的服务和克服的障碍面前,有组织地进行团队行动。我们看到了诸如“生命之歌公益论坛”这样一路坚持,发动各地志愿者,动员各地资源,组织大型轮椅团队出游的自发组织;也看到了由官方支持的中康残疾人旅游俱乐部的成立和博爱之光残疾人康复旅游活动的发展;还看到了四川圆梦助残服务中心这样的民间助残组织以政府和学术资源为依托,推动的“圆梦之旅”无障碍爱心联盟和四川师范大学无障碍旅游研究与发展中心。他们不仅组织肢体障碍人士出游,也逐渐转向将无障碍与出游结合,形成一种在旅游中促进无障碍发展,在无障碍发展中继续旅游的模式,为残障人旅游增添了一个重要的附加值和不同于非残障人的正当性。这一认知,在2015年5月于四川举办的全国首届无障碍旅游发展论坛上得以明确。而近两年来,视力障碍人士也纷纷加入“出走”的行列,更是对“无障碍旅游”的意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2017年,我们看到上海知了公益文化传播中心推出的残障人士迪斯尼专线游,结合其无障碍状况,根据残障人的情况提供订制服务,在无障碍的基础之上,看到了残障人旅游品质的关注与探索,似乎又给了残障人出游一个新答案。
而中国残联发布旅游年卡,显然是这些年在官方与民间的积累与推动下所释放的一种信号,关于残障人旅游已然产业化的信号,号召旅游业全面提升自我,更好地服务于残障人的需要与要求的信号。
但是这种信号会被怎样解读,又会催生出什么样的服务?是又一次各方参与利用残障的收割,还是每个残障人切实利益的促进?最终写下这篇老残游记的,不是某个组织,也不是某个残障名人,而是每个残障者。
黑科技
文/蔡聪
随着2016年人工智能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全世界在或喜或忧中惊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在这个新时代下,残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离真正被“消灭”已然不远。
2017年,人工智能火爆依旧。如果自动驾驶全面应用,那盲人也可以开车。而人工智能能够剪辑恐怖电影的宣传片,那显然离读懂人类的情绪,与自闭症人士良好沟通亦不远。但是,当人工智能在残障领域稍慢一步于2017年呈现之时,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眼前一亮的黑科技和关于人类的想象力,而是仍旧以医疗和功能补偿为主的换汤不换药。
导盲眼镜、导盲腰带、导盲头盔、导盲太阳帽……被冠以人工智能技术之名的各类科技产品,纷纷向残障人发出邀请,在一轮又一轮的测试与体验中,人们畅想着技术能够让盲人重见光明。而对此最为激动的,显然是我们的家长。而很多从来就没有见过光明的盲人,还停留在“就算我真的能看见了,那为什么要叫重见呢”这一疑惑之中,更何况,这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看见。
当轮椅不再是为了代步,而是让你重新站起,当盲杖不再是为了帮你扩大信息感知范围,而是试图让你看见,当APP只是将声音转成文字,却并不关心究竟什么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之时,即使我们有再多的黑科技,对于要使用它的人来说,在这个仍旧将你视为不正常和要揪正的环境中,也只能永远是科技而已。
录取
文/蔡聪
随着2017年4月《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正式颁布,残障人高等融合教育的大门似乎就此敞开。6月高考过后,高考放开之后必然要面临的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大学到底应该如何应对残障大学生的到来?
这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2017年尤为突出。围绕甘肃轮椅考生魏翔与清华大学的互动,以及安徽视障考生王宠与东北师范大学的互动,同样是因为宿舍,轮椅考生写信只求学校给陋室一间以供其母陪读,学校回信鼓励,网友一度被感动与温暖刷屏;而盲人王宠的学校,却因劝其校外租房且带母陪读引发骂声一片。
在这个过程中,想必高校都有点懵,不知道这些残障学生到底要闹哪样,后面还会不会带来更多麻烦。显然,录取之后的合理便利如何提供,已然来到台前。
录取就像结婚,它不是童话里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是《亮剑》中抠脚大汉李云龙和旗袍碧玉田雨的生活的开始。不管清华与东北师大如何,其他高校有没有反思,我们都知道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而推动这个过程加速的,是残障人本身。在清华回信刷屏后,有残障人组织以“清华还欠我们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为题展开传播,也有残障人组织起来到清华进行轮椅无障碍体验,这都是通过主体的参与来推动问题从感动中走出,迈向制度化的解决。而东北师大面对舆论压力,邀请了北京声波的视障人专家来为王宠做评估、出方案,让我们看到了未来DPO以专家的身份平等参与各项事务的可能。
但当我们以为这就是方向的时候,9月又出现一起浙江工商大学城市学院将视障学生“劝出”宿舍,却无多少媒体关注的事件,让我们从清华的那则“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相信”里读出了“人生实苦,但请你足够优秀”的感慨,也对更多不是那么优秀的残障学生能否被录取,以及录取后有什么机制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产生了担忧。
盲怒
文/蔡聪
2017年3月20日,国内多个盲人论坛出现一份名为“视障者抵制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的联名信”的签名帖,该帖未见发起者署名,号召视障人士抵制该机构。
该机构自2014年以专业的身份进入信息无障碍领域,并为国内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提供信息无障碍测评服务以来,与视障群体数度爆发矛盾。视障群体的指责主要在于该机构垄断话语权,使合作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不再直接与视障群体沟通,同时该机构参与的诸多APP信息无障碍改进工作结果都是越改越糟等。该机构负责人也多次回应表示他们同样雇用了视障员工,并不是健全人代言,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对于那些公司产品他们只有评测与建议权,但无最终决定权,也没有阻拦视障群体的参与,但视障群体仍旧多次在各大盲人论坛和微博等公开平台进行抵制,直至这次两千多名视障者签名联合抵制。
我们大多数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即使是当事人,也无法断定自己所见即真相,但是对于视障群体的“盲怒”,有一些观察与思考。因为它直指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核心,“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有关我们的决定”,以及第四条和第三十三条所言明的残障人组织的参与。参与并不是简单地出现在现场,而是有一全套支持机制和公平议事机制保障下的信息充分获取与理解、意见充分表达与被聆听和是否采纳的明确反馈与讨论。而参与者对于社群的代表性,更是社群所在意的事情。
看似这是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与视障社群的矛盾,但这种怒气的爆发,根本上是充斥在各行各业的助残组织(Organization for Disabled Person)和社群自身期待但无什么地位的残障人自助组织(Organization of Person with Disability),for与of之间话语权的争夺。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组织将“参与”解释成他们的机构里也雇用了“残疾人”之后,更让残障人难以在非残障人占据话语权的场域里发出声音。所以出现了残障社群“盲怒”的情况,因为他们只剩下了情绪表达的空间,只剩下了“不理性地”“盲目”表达情绪的空间,甚至不管在非残障人居多的以怜悯同情为基础的公共空间里,人们会如何看待这群人。但是从国际残障权利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愤怒恰恰就是社群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只是在中国讲求阴阳平衡、凡事不可太过的文化里,显得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不知感恩。
因此,我们看到的盲怒来自盲人的自发,诸如北京声波这样的盲人社群组织,却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参与与支持。可能他们受限于残障人社群本就可怜的资源,不敢得罪人,可能是他们已经过了情绪爆发期,更关心如何纳入更多的利益相关方来推动改变。但是作为伞形Umbrella的DPO组织一加一,在2017年12月10日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残障项目共同面向科技企业发布了《关于科技产品遵守信息无障碍相关原则的北京倡议》,专门提出残障人及其代表组织在科技产品的各个环节过程中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对我国相关法律的期待,延续了这场盲怒。在情绪中探索方向,也为未来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待中国残障权利运动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因果。
拜托
文/蔡聪
2016年,中国智协、广东智协发起全国特殊家庭养老+托养调研项目,北京、岳阳等地相继成立了侧重点不同的服务养老+托养机构。心智障碍人士家庭的父母养老问题以及父母逝世后心智障碍子女的养老问题,近年来越发受到关注。心智障碍子女随父母一起入住养老机构进行家庭式托养,父母逝世后财产信托以支持子女生活及托养,成为应对心智障碍人士尚很难融入社会的无奈的现实策略。
虽然这些讨论由来已久,且也得到了一些官方回应,但随着2017年5月9日广州一位83岁的老人将46岁的智障儿子杀死这一事件的报出,再度引发广泛的讨论及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新一轮的焦虑高峰。
诚然,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是社会支持系统不完善的悲哀,也看到了心智障碍人士家庭支持系统需求的迫切性,但有些显得不合时宜的探讨也有必要在2017年提出,并且留下痕迹。
心智障碍人士家庭在父母老迈之时的子女双托模式,被广大家长普遍认同并期待,但这是以家长的需求为核心,并非心智障碍人士自身权利的最好体现。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融入社会并且独立生活,和非残障人一样地发展,才是其最根本的权利与需求。虽说这种选择里带着一些现实系统不完善的无奈,但当我们一边倒地去呼吁双托,理所当然地认为家长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最能代表自己孩子的权利之时,应当跳出现实,多一些反思。呼吁双托,确实符合家长的利益,也至少不会让心智障碍人士无人照料,但那些可能还不是紧急需要这些的家长,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倡导的空间中时,是不是应该去反思,或者推动心智障碍人士自主决策、独立生活的支持系统,而不是看似一劳永逸的各阶段托养工程呢?
残障者站在自身的残障上,有局限;而家长,这个与残障本来无关,却又被迫有关的群体,站在家长的位置上,同样有自身的局限。我们可以顺应这些局限,就此放弃,但我们更想拜托家长看到这些局限,选择逆流而上。
爆效
文/蔡聪
谈到2017年中国公益发展的状况,有一件事情注定不能绕过,那就是刷爆网络、半天筹款1500万元的“一元画作”。这次成功的传播与筹款,是很多公益机构梦寐以求的,也是资助者无比期待的。然而,传播得有多广,有多成功,引发的争议就有多大,有多深。这件事情之于残障领域来说,最大的反思在于它是否在利用公众的同情,加深自闭症人士的刻板印象,让自闭症人士只能以儿童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并且拥有艺术天赋,这才是有价值和值得关注的。显然,这样的效果,从残障人士和家长组织的角度都不期望看到。
而在这样一个爆点之后,又有一个没能爆起来的残障项目,一开始传播便遭遇巨大质疑。它是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于2016年发起的橙色书包项目。当它因为明星的参与进入公众视野,呼吁大家“看到背橙色书包的孩子放慢车速”之时,不仅遭遇残障人组织认为其“隔离化”“标签化”的质疑,也被有些人调侃道“遇到其他孩子那要不要踩油门”。
当然,在一元画作和橙色书包的背后,还有关于捐款的去向与监督的讨论、橙色书包价格与采购程序的讨论等。但这些讨论最终都被有没有成为爆点所淹没。而这样的对爆点的追求,对巨额捐款的追求,自腾讯举办“99公益”以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益机构发展的面前,有可能出现因为走得太远、走得太快,却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的情况。因为一切都走向配合资源导向,迎合公众关注导向,而不再是问题解决导向,也不再是从公益出发,去影响和改变更多人。
一个爆点的效果,可能是使人们记住了这个爆点,但是它背后的讨论与反思会渐渐模糊。所以,我们需要记录。
对于爆点的追求与效仿,是资源不均衡导致的行业生态,但就如同高考,在疯狂训练得高分的经验分享之余,从中跳出来看到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应该更为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