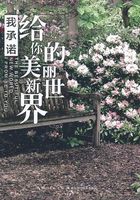
我的“理想国”
我的旅行就将结束在前方那个飘荡着五色风马旗的丁字路口。明天,香格里拉这片暮霭中的大河雪山、丛林草滩,又将重新回到我床头柜上那本装帧精美的小说里,留待日后某个偶然翻看的夜晚,再次找寻和体味那种终于来到世界某个尽头和归宿的感觉。
——摘自《雪山与大河之间》 作者 兔毛爹

我家的小屋和一幅充满了乌托邦式空想色彩的佚名油画有关。在我众多收藏品中,它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
喜欢旅行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从世界各地带回些奇珍异宝。在我家的各个角落里就散落着柬埔寨的佛像、印度的烛台、海地的木雕和墨西哥的陶偶等。这些收藏品通常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让人看上一眼就能回忆起当年曾经到过的某一个阳光明媚的旅行目的地,抑或某一段不算平坦的泥泞旅途。
唯有挂在餐厅里的一幅画,我却不能说清它的出处,只是当年听卖画的人讲:此画出自一位流浪画家之手,笔下描述的是他曾经的梦境和醒来后的思考的过程……
画家在画作的中上部,为欣赏者精心布置了一个凸起并悬浮在半空中的幻象山庄。山庄里坐落着具有17世纪田园风格的尖顶小屋和架着梯子的谷仓。一条石径蜿蜒向前,将人的视线吸引至山庄前地势较低的井台。井畔是一位提着桶的乡村少妇。井中,一条细细的井绳和低垂的水桶,仿佛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拉扯着欣赏者的目光去探索画作下方,那一片凹陷在深谷之中,波澜不惊的神秘水潭。水潭边,是一条伸及旷野的无人栈道,远方则是一片片若有若无的白色浮云和紫色山峦。


虽然,从总体上看,这幅画给人一种简单、祥和,甚至平淡之感。然而,画中那些石路、深潭、井绳和栈道,却总能出其不意地涤荡起欣赏者灵魂深处某些说不清的幻象冲突和莫名向往。
我常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或是满天星斗的夜晚,静静地凝望这幅充满了暗示和象征意义的图画。看得久了,画中那座与世无争的尖顶小屋,竟不知不觉成了我内心中那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而那片象征着思想源泉的深潭则最终成了我潜意识中那个超现实的归宿所在。
人唯安居,方可乐业。那么,我眼中的“理想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自幼生活在北京的胡同,所以对过往的四合院生活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20世纪70年代,我住在北京崇文区河泊厂东巷50号,一座属于中国文联的宿舍院里。同院的邻居中有和启功齐名的古典文学大师陆工,也有现代京剧《沙家浜》的作者汪曾祺。有了这些文坛“活宝”的存在,可想而知,当年胡同的生活会有多么丰富多彩了吧!而那句红遍大江南北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其实就是那个年代,文联宿舍夏日夜晚葡萄架下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北方的夏日,人们通常是坐在四合院的屋檐下吃晚饭的。有时,仅仅因为出差的人从外地带回了一两瓶好酒,各家的饭桌就凑到院中间的葡萄架下了。文人相聚,不免贪杯。不过喝多了也没关系,胡同的东头还住着个名医,叫贾梦莲,绰号“贾三针”。据说,不论多大的病,求他扎上3针准好。过去的中医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所以他扎针灸从不让女人脱衣服,而是隔着棉裤直接扎。我长大后总是想:贾三针的针法固然好,可他这么干卫生吗?不过,卫不卫生法都没关系,反正现在的北京也不再有河泊厂那样的胡同和贾三针那样的神医了。



因为儿时的种种经历,我至今仍喜欢带兔毛到后海、西四一带老北京的胡同里转悠。我以为建筑即文字,长期穿行其间的人一定会耳濡目染,受到这些建筑自身所传递出的文化信息的影响。所以说,胡同是一本本无形的书,唯有置身其中,才是对历史最好的阅读和解读。

然而,近30年来,我童年记忆中的“理想国”业已没落和衰败。(自1990年开始,大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人都搬到北京三环路以外的商品楼里去了,胡同里留下的大多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居住环境的老人和外来的租户。)胡同的现状常让我痛心疾首、扼腕顿足。
15年前,我买下了位于望京的一栋25层楼上的一间公寓。天气晴好的夏季清晨,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举目向南,即可眺望北京城里那些摩登大厦“婀娜的背影”。而在夕阳西下的冬季傍晚,面北远观,则可看到遮天蔽日的飞鸟,匆匆掠过远方的杨林大道寻找归宿的瑰丽画面。
那个时代的望京,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地。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刚好契合了“进,则入世;退,则入山林”的中国式人生观。
但是,没几年的光景,那些“婀娜的背影”竟不知不觉地“蜿蜒”到了我的眼前。这个当年被人们戏称的“大卧城”,仿佛一夜之间被唤醒,匆忙披上“闹世”的外衣,兴高采烈地加入摩登时代都市狂欢的行列中了。
兔毛出生的时候,我家那个曾经看得见风景的阳台早已变成了高楼大厦中的“天井”。站在天井里,即可感受市井的缭乱与嘈杂和汽车尾气的扩散与蒸腾。于是,睡在“万家灯火”里的我开始寻思着“迁徙”。为了躲避日益严重的雾霾,也为了给刚出生的兔毛创造一个无拘无束的生活空间,我下决心穿越远方的杨林大道,去寻找属于飞鸟的丛林、大河、草地和花园。
